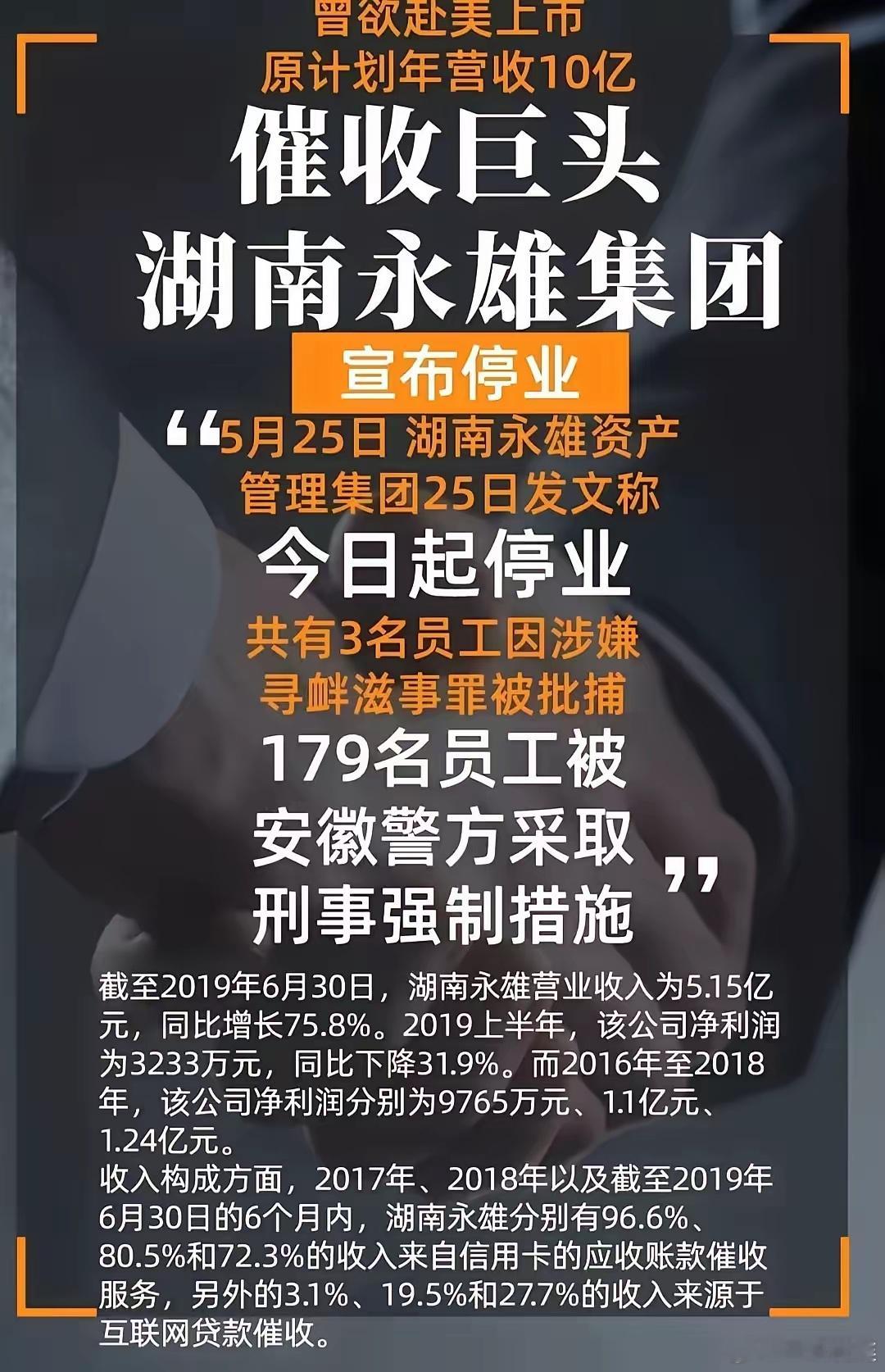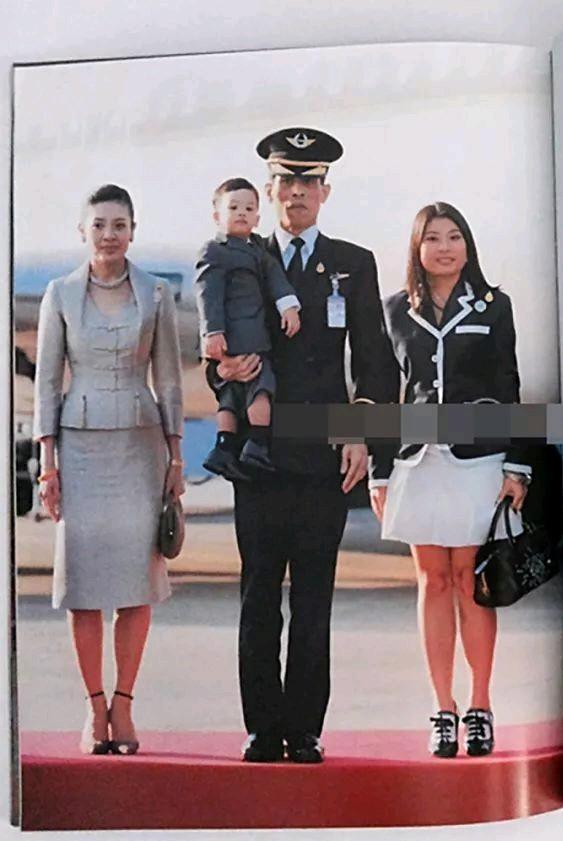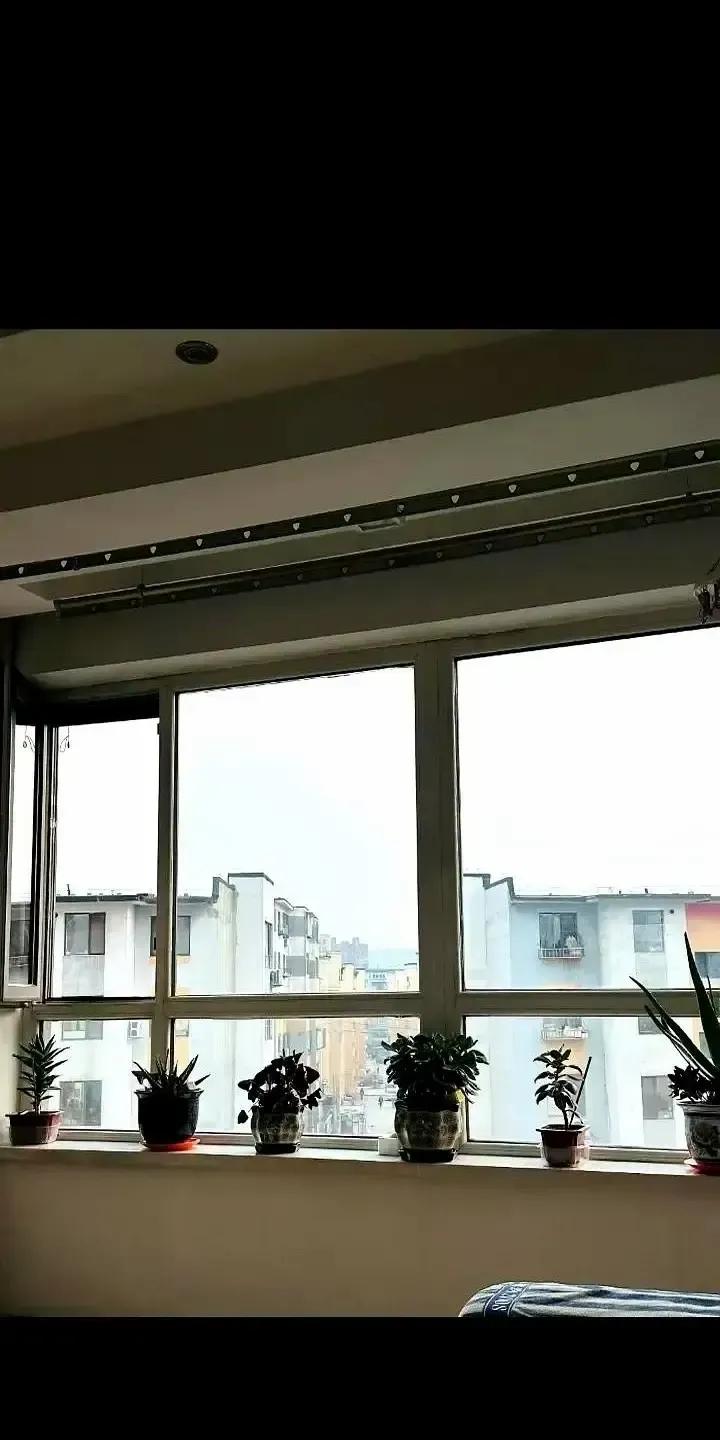1933年哈尔滨的冬天,一张刑场合影成了历史的伤口。 照片上十个人站在雪地里,九名男性胸前挂着铁链,唯一的女性低着头,发丝被寒风掀起。 他们是哈工大的学生,也是抗日义士。 三天后,枪声在城外荒地响起,《满洲报》说这是"破坏分子"的下场,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伪满洲国的课本里,"日满一体"的课文印得鲜红。 哈工大教室里,日语成了必修课,黑板上写着"共存共荣",学生们却在课桌下传纸条,上面是用俄语写的抗日诗句。 1935年苏联卖掉中东铁路后,学校开始换日本校长,但早在1932年,任震英就把伪国歌改成了战歌。 "建立人民自立政府"的歌词,藏在俄文教材的夹页里传遍全城。 侯竹友家的俄式壁炉总烧得很旺。 这位女教师把药品藏进煤堆,父亲用警察秘书长的身份打掩护,母亲和嫂子在厨房开会时总把水龙头开得很大。 有次伪警察突袭,她把传单塞进孩子的棉裤夹层,笑着说"这是给游击队的尿布"。 后来她出现在那张刑场照片里,低头的姿势像在保护什么。 松花江结冰时,学生们在冰面凿洞藏传单。 零下三十度的夜里,有人背着粮食给游击队送补给,睫毛冻成冰碴也不敢靠近火堆。 孟昭麟把铁路图纸画在卷烟纸上,假装醉汉跌进抗联营地。 这些工科生用专业知识当武器,把课堂变成战场。 2024年哈工大博物馆里,AI修复的老照片旁摆着《反满抗日新歌》手稿。 参观者不知道,展厅地砖下藏着二维码,扫码能听到侯竹友学生回忆她教唱《红旗歌》的声音。 今年清明,有人在烈士墙前放了束冰凌花,卡片上写着"你们的课,我们还在学"。 现在的实验室里,学生们调试芯片时,屏幕保护程序会弹出老照片。 那些没有名字的青年,成了"红色工程师摇篮"的精神坐标。 他们的牺牲没能立刻改变什么,但就像松花江冰层下的水流,默默积蓄着冲破寒冬的力量。 如此看来,有些丰碑不需要名字。 当我们在芯片上刻下"中国芯"三个字时,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完成他们未竟的实验报告。 那些在1933年冬天选择站着死的学生,早把答案写进了民族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