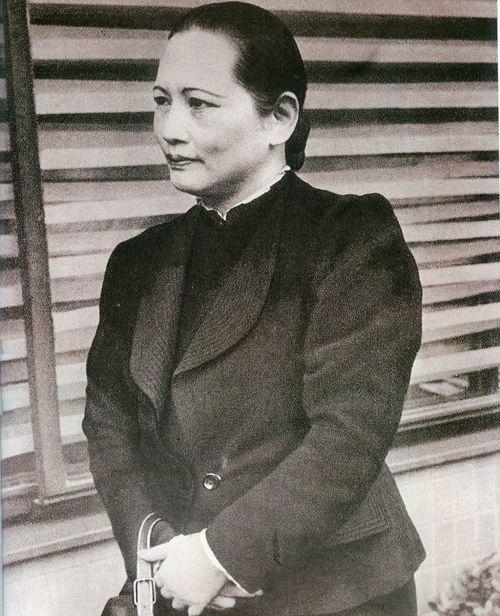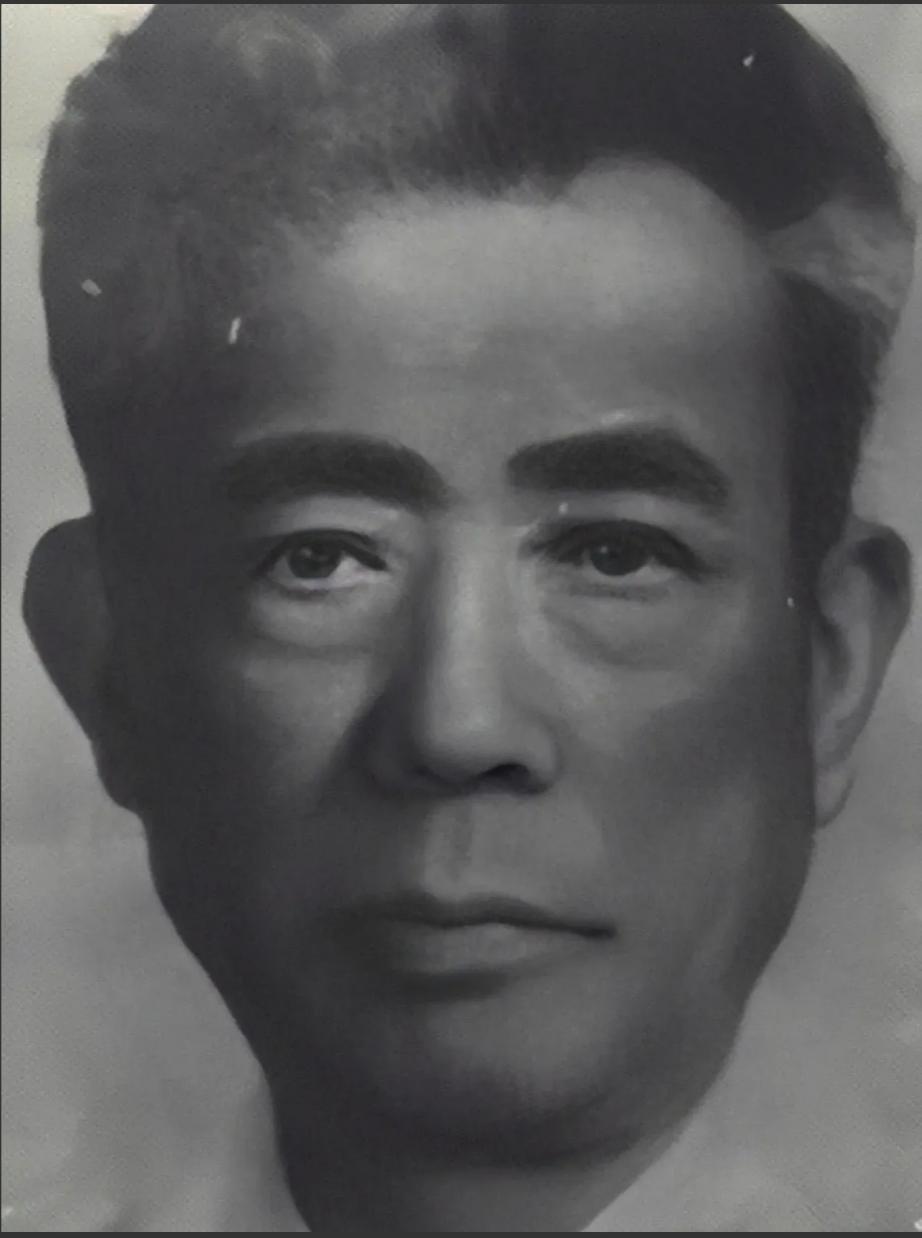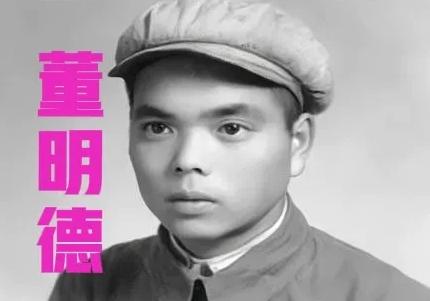1899年5月4日,一个刚刚分娩的女人,指着她刚出生的女儿,大声说道:“快把这个灾星抱走,我不要见她!” 在福建闽侯县岭东村的产房内,一声啼哭撕裂寂静。 新晋举人黄宝瑛的妻子盯着襁褓中的女婴,猛地抓起棉被盖住脸。 当日恰逢外祖母离世,这个女婴便成了她宣泄丧亲之痛的替罪羊。 “快把这个灾星抱走!” 拒绝哺乳、丢弃奶妈、无视啼哭,家人的冷漠如影随形。 三岁那年,父亲调任长沙知县,母亲一句“不带灾星上路”,将她遗弃在叔祖母家。 寄人篱下的日子毫无温情,叔祖母的叹息“累赘”二字,成了她童年最常听到的评价。 六岁那年,父亲病逝的噩耗传来。 母亲再次将丧夫之痛转嫁到她身上,认定是她“克死”了父亲。 失去经济来源的黄家举家迁往北平投奔舅舅,却唯独忘了这个远在福建的女儿。 直到九岁那年,走投无路的叔祖母将她塞进免费教会学校。 严苛的校规与体弱多病的身体让她屡陷险境。 脚疮险些致残,肺管破裂吐血数次,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十岁那年。 母亲终于想起这个被遗忘的女儿,将她接到北平。 然而等待她的不是母爱,而是更深的伤害。 洗衣扫地等杂活取代了读书的权利,打碎一只碗换来的是鸡毛掸子追打。 “丧门星”的辱骂声中,哥哥们的冷眼旁观更让她明白,在这个家,她永远是多余的人。 庐隐在哥哥们读书时偷偷蹲守窗外,记下先生讲授的每一个字。 煤油灯下,她将偷学来的知识反复咀嚼,用树枝在沙地上默写生字。 这种近乎自虐的学习方式,让她在191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当录取通知书送达时,母亲第一次对她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个被判定为“灾星”的女儿,竟真的靠读书改写了命运! 在女师校园里,庐隐剪去象征束缚的长发,穿上男式套衫与短裙,成为校园里特立独行的风景。 与苏雪林等同学组建的“六君子”团体,常在月下畅谈妇女解放的理想。 梁启超、鲁迅的文章如明灯照亮前路,她开始用笔记录被压抑的女性心声。 1919年,庐隐以旁听生身份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在国文部的课堂上,她系统学习文学创作理论。 当第一篇短篇小说《灵魂可以卖吗》发表在《小说月报》上时,这个曾被家族唾弃的女孩,终于在文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而庐隐的情感经历,也如同她笔下的小说般跌宕起伏。 第一段与表亲林鸿俊的恋情,始于她对封建婚姻的反抗。 当母亲以“门不当户不对”反对时,她掷地有声地写下“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然而婚后发现对方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后,她果断解除婚约,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清醒。 第二段婚姻带给她的却是更深的创伤。 与有妇之夫郭梦良的结合,让她陷入道德与情感的漩涡。 不仅要面对原配妻子的挑衅,更要承受社会舆论的指责。 当郭梦良因积劳成疾去世后,27岁的庐隐带着幼女独自面对世界的恶意。 《海滨故人》中那些在爱情中迷失的女性形象,正是她自身经历的投射。 1928年,比她小9岁的清华诗人李唯建闯入她的生活。 这段“姐弟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却让庐隐重新相信爱情。 他们在日本东京郊区的同居生活,催生出《东京小品》等清新之作。 然而婚姻的浪漫,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残酷。 李唯建沉溺诗歌创作,对家庭责任漠不关心。 庐隐不得不同时扮演作家、教师和母亲三重角色,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1934年的难产成为庐隐生命的终点。 为了节省医药费,她选择花10元钱请街头助产婆接生。 混乱中,刀片划破子宫的剧痛伴随着婴儿的啼哭,这位在文坛叱咤风云的女作家,最终倒在血泊之中。 36载人生,她留下了12部作品集、80余篇中短篇小说,共计150万字的文学遗产。 庐隐的早逝令人扼腕,却也为她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中,她被列为18位重要现代女作家之一。 那些曾被家族视为“灾星”的特质,最终化作笔尖流淌的文字,成为照亮女性解放道路的火炬。 当我们在百年后的今天重读庐隐的作品,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灼人的力量。 这位被历史尘埃暂时遮蔽的才女,终将在文学星空中绽放永恒的光芒。 正如她笔下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女性,永远在提醒我们,即使生而为“灾星”,也能活成照亮时代的星辰。 主要信源:(微信公众平台——这名从福州高新区走出的才女,以觉醒女性身份登上“五四”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