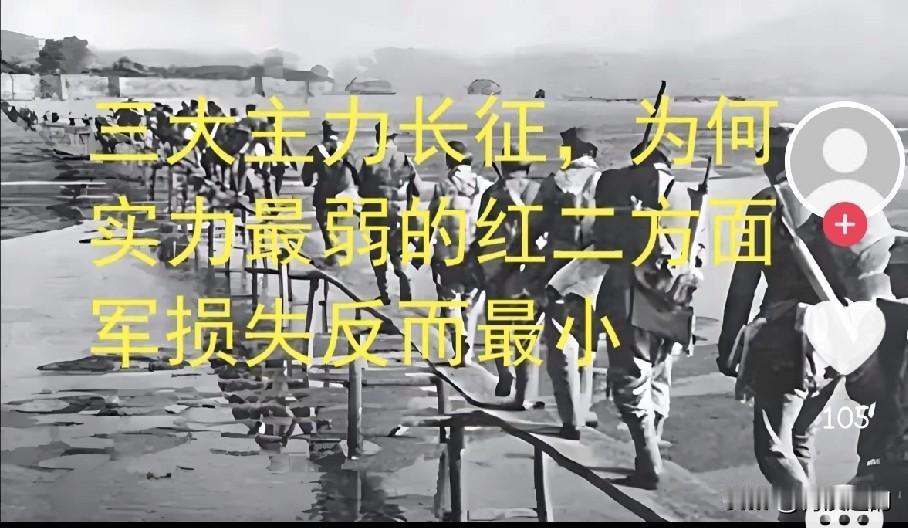1935年,他被开除党籍,戴着手铐走完长征,开国大典前,毛主席问他:“你为何不来看我?” 朱光站在中南海书房门口时,神情平静,心却跳得极快。门内传来熟悉的笑声,他本以为只会见朱老总,却没料到毛主席也在。 主席一见他,眼带笑意:“你是哪个?”朱光微微一拱手,嗓音洪亮:“朱光是也。”主席佯装惊讶:“既然认得我,怎么先去找总司令?”他咧嘴一笑:“同姓同宗,门近亲熟嘛!”话音未落,两人哈哈大笑,像多年前在战火硝烟中争夺那本莎士比亚名著的场景重演一般,隔着十多年光阴都还清晰如昨。 可若回望十四年前,这位站在领袖身边的干部,曾一度背负“右倾机会主义”之名,被开除党籍,戴着手铐走完了长征。 那是1935年,小河口会议上,朱光顶撞张国焘,反对其分裂路线,结果触怒“上峰”,一纸处分将他打入“政治冷宫”。可张国焘没有杀他——不是出于宽恕,而是朱光那手过硬的书法与制图本领让他舍不得。 就这样,一个“囚徒”被捆上镣铐随军长征。他白日扛着沉重的油印器材翻山越岭,夜晚在篝火边刻蜡板、画地图、写标语。“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一句句标语贴满村寨,也贴进百姓心里。 三次爬雪山,脚腕处的镣铐早磨出血痕;三次过草地,断粮时他啃草根吞树皮,硬是咬牙挺了过来。有人劝他低头认个错换口热饭,他只淡淡一句:“人可以低头写字,信仰不能低头过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那段戴铐的岁月,磨出他日后的刚硬脊梁。 1936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宁夏,朱光终于等到平反。他摘下镣铐,捧着恢复党籍的通知,没哭,却写下“苦难,是最锋利的刻刀”。 抗战爆发后,他奔赴太行山,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任秘书长,又转战冀南、冀鲁豫多地,宣传抗日、稳定人心。滑县、浚县战场上他随军奋战,时常深入敌后组织文宣和群众工作;新四军游击区的广播稿、战地通讯里,时常能读到他的文字。 建国后,他南下接管广州。广州是座偏重商贸的城市,他却从工厂干起,推动造纸厂、机械厂扩建,为这座城市注入工业血脉。他提出“绿化广州”的理念,亲自栽种木棉,后来竟成城市象征。他还主持兴建华侨新村,保障侨汇归国,让漂泊的赤子安心落地。 毛主席私下称他“江南才子”,可他的才情,从未用来吟诗赋词,全落在实干中。 有年暮春,他再次进京述职,毛主席问他:“你还记得咱们那场‘夺书战’吗?”他一笑:“记得,我还记得你当时不肯让我拿《奥赛罗》,说我不配演那角色。” 主席笑着挥笔写下一首《长征》送他,他则回赠:“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毛主席看完,笑道:“你诗中写‘书法家之府’,我改成‘书法癖之家’更妥当。”房中一时笑声四起。 他把这句话刻在心底,也将“到南方去,将工作做好”作为毕生的任务。广州十余年,他未建别墅,不留名利,城市变了模样,他却仍骑自行车穿街走巷,问菜贩、听民意。 朱光的一生,是跌宕,是砥砺,也是信仰的坚守。他曾在历史最寒冷的季节里戴着镣铐写出温暖人心的文字,也曾在和平年代用手中笔墨为城市描绘新貌。他不是传奇的创造者,却是传奇的一笔。 信仰之所以伟大,不在它高高在上,而在于——即使在手铐脚镣之间,依旧有人选择背着它走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