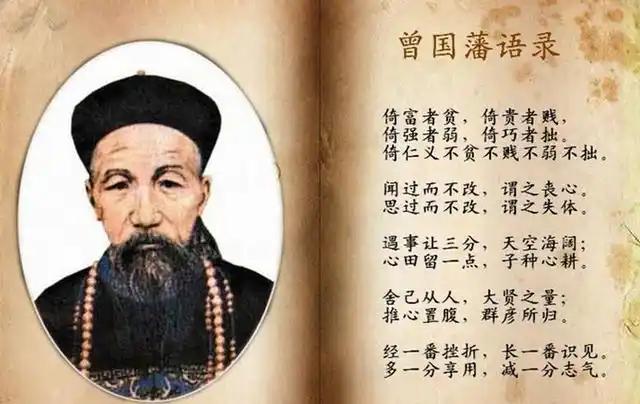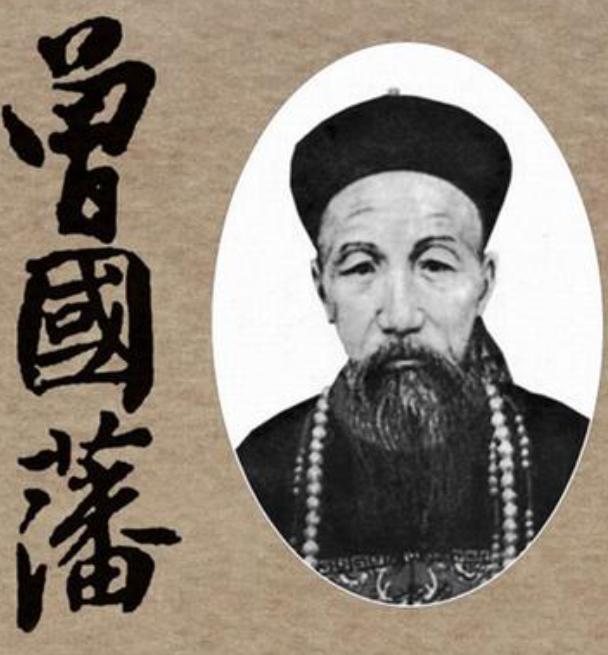朝廷不给湘军拨款,而且将士的待遇又高,曾国藩从哪里弄这些钱? 咸丰三年,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办湘军,一开局就撞上了天大的难题——朝廷压根没打算给这笔军费。可他招兵有个死规矩,待遇必须比绿营军高两倍以上:普通士兵每月三两六钱银子,比绿营兵多三两;营官月薪五十两,外加两百两办公费,要是打了胜仗还有重赏。 这可不是小数目,一支万人军队每月光军饷就得四万多两,曾国藩愁得头发都白了,可再难也得想辙,弟兄们要吃饭打仗,总不能让人家空着肚子卖命。 最先让他抓住救命稻草的是“厘金”,说白了就是商业税,过路费、交易费都算。1854年,曾国藩在湖南湘潭设了第一个厘金局,规定凡是过境的盐、布、茶叶,每值一百两就抽一两五钱。 这招一开始遭商人骂,可架不住曾国藩铁腕推行,派湘军直接守着水陆要道,不交就扣货。湖南当年的厘金就收了二十多万两,刚好撑住了湘军最初的开销。 后来他把这招用到江西、安徽,光江西景德镇的厘金局,因为靠着瓷器和茶叶贸易,每月就能抽三万多两,占当时湘军月饷的七成。 有回江西巡抚跟他抢厘金,曾国藩直接上书朝廷,说“湘军守江西,却无饷可领,何以立足”,硬是把厘金大权抢了回来,这钱才算是稳住了大头。 打胜仗抢缴获,是湘军最“痛快”的筹钱办法,曾国藩管这叫“打活仗”。1861年的安庆之战,曾国荃带着一万湘军围了安庆整整一年,城里的太平军攒了八年的家底全在这儿。破城那天,湘军士兵从太平军将领府里搜出的金银珠宝,用担子挑了三天三夜。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里说“安庆所获之资,足供全军半年之饷”,实际算下来,光是金银就有两百多万两,还有几十万石粮食,不仅解决了军饷,连过冬的棉衣都有了着落。 最狠的是1864年打天京,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的国库抄了个底朝天,虽然具体数字没准头,但从曾国藩后来主动裁撤湘军就能看出来——有钱才能底气十足地裁军避嫌,不然几万张嘴等着吃饭,他哪敢裁。 地方士绅的捐助,是曾国藩初期的“启动资金”。他自己是湖南士绅领袖,找亲戚朋友带头捐,再逼着地方富商出钱。 湘乡大商人朱昌琳,一开始只肯捐两千两,曾国藩亲自上门,拿出自己的官印说“你捐十万两,我保你子孙后代有功名”,朱昌琳吓得赶紧掏钱。 湖南、湖北的士绅前后捐了一百多万两,虽然比不了厘金和缴获,但在湘军刚起步、没人敢信的时候,这笔钱救了急。后来他还搞“捐纳”,就是卖官,捐一千两给个九品官,捐一万两给个五品官,光1855年一年,湖南就靠这个收了三十多万两,不少商人想着买个官面儿,心甘情愿掏腰包。 还有些“零碎”办法,凑起来也不少。他截留地方漕粮,把本该运到京城的粮食低价卖掉换钱;又跟外国商人合作,垄断了长江的盐运,每包盐加抽一两银子的“湘军专饷”。 有回英国商人偷偷给太平军卖粮,曾国藩直接派炮船把商船扣了,逼着英国领事保证不再犯,还罚了商人几万两银子充军饷。这些办法看着杂,可每一笔都透着无奈——朝廷不给钱,他只能当这个“抢钱的恶人”。 最让人佩服的是,曾国藩把每笔钱都管得严严实实。他设了专门的粮台衙门管收支,每月军饷发完都公示,谁也别想中饱私囊。 有个营官私吞了五百两,他当场砍了脑袋,从此没人敢乱伸手。靠着这些硬招,湘军十年间花了三千多万两军饷,朝廷只给了不到三百万两,剩下的全是他一点点凑出来的。 说起来,曾国藩不是天生会筹钱,只是为了平叛保国,不得不硬着头皮把能想的办法都试了个遍。 那些骂他“聚敛”的人,没见过湘军士兵冻着肚子打仗的模样,更不懂他“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心思——要是没钱养兵,太平天国的战火早烧遍全国了,哪还有后来的安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