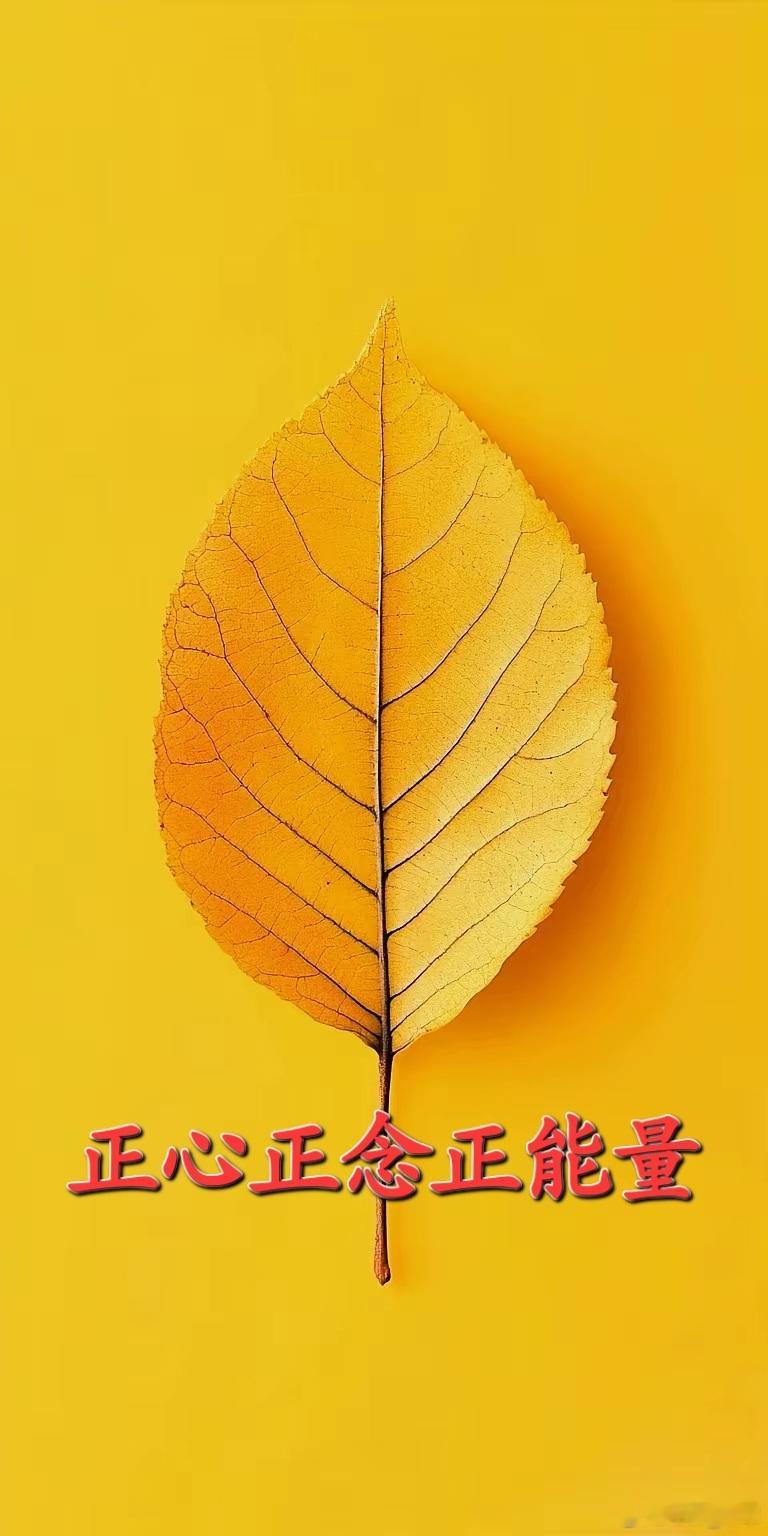张锡纯用鸡内金的三大经典搭配!张锡纯在他的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对许多中药都进行了新的理解和应用,其中对“鸡内金”的运用尤其精彩。鸡内金,就是鸡的砂囊内壁,古人常用来消食导滞。白术性温而燥,能健脾利水、止泻除湿。若单用白术,补而不化;单用鸡内金,又恐其性偏行化,伤及中气。所以他强调两者搭配,一攻一补,既能健脾,又能消积。比如他所创的“化瘀通经散”,就用炒白术、生鸡内金、天冬等药共研成细末,以开水送服,既通经活血,又不伤中气。张锡纯还细分炮制方法:生白术偏于行血通瘀,炒白术更善健脾止泻。如此灵活运用,使药性平衡、效力更显。他说得好:“补脾不壅滞,化瘀不伤正”,这正是白术与鸡内金相得益彰的奥妙所在。鸡内金与山药的搭配,则体现了张锡纯对“脾肾同调”的深刻理解。山药性平味甘,入脾、肺、肾三经,能补气养阴、强健脾胃。张锡纯强调山药宜生用,因为生山药富含蛋白质,若炒焦则其精华尽失。在《资生汤》中,他以生山药配合生鸡内金、玄参、牛蒡子,用于女子血枯不月之症。山药补脾肾之阴,鸡内金健脾化积、促进血生;再辅以玄参滋阴、牛蒡子疏风,使气血调和、月经自行。张锡纯称这三味药为“补气健脾不可挪移之品”,足见其地位之高。他认为补脾肾阴阳、调气血升降,是调经、治虚劳的关键,而鸡内金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再说鸡内金配生麦芽。麦芽是谷芽之体,善消食、行气、疏肝。肝属木,木性条达,麦芽入肝可助肝气升发。鸡内金则能助胃运化、消坚散结。张锡纯利用两者“一升一降”的特性,让气机升降平衡、脾胃调和。比如有位妇人,因胁痛、饮食停滞多年不愈,他用生麦芽四钱、生鸡内金二钱、生山药一两,连服十剂病愈。张锡纯解释说,肝左不升,胃右不降,就会气滞食停;麦芽能升肝,鸡内金能降胃,气机调顺后,疼痛自解、饮食自复。这个思路,就是《内经》所谓“厥阴不治,求之阳明”的活用。他看重的不是单一药效,而是“脾胃升降”的整体和谐。除了这些配伍创新,张锡纯还把鸡内金的作用延伸到替代西药的领域。在他那个时代,西医刚传入中国,很多人尝试把两种医学结合。张锡纯认为,鸡内金来自鸡的消化系统,而西药“百布圣”(即胃酶制剂)源于猪或牛的胃液,两者在性质上可类比,皆能帮助消化。他提出“以脏补脏”的理论——既然鸡内金能健脾化积,就能代替或辅助这些西药使用。例如在治疗痰喘、食积阻滞等病时,若病人痰多不化,他常用鸡内金代百布圣,以健脾化痰、助运消积。现代研究也印证了他的见解:鸡内金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加消化液分泌,甚至能解除胃肠痉挛,其效与阿托品相似。从这些医案中可以看出,张锡纯对鸡内金的认识突破了“单纯消食”的旧框架。他把这味药放在整个脾胃系统的调理中来理解:既能“化积”,也能“生化”;既能“通滞”,也能“养正”。他重视“中气”与“血气”的互动,讲究药性之间的平衡。正因为如此,鸡内金在他手中,既能治食积、痞满、泄泻,又能通经、调血、化瘀,甚至用于虚劳与代谢类疾病。更重要的是,张锡纯的这些用药思路,反映出一种“中西融通”的精神。他不盲目排斥西医,也不照搬,而是用中医理论去解释和吸纳。他看到鸡内金与动物胃液之间的相似,就大胆提出“以形补形”的替代思路;他分析脾胃阴阳升降的关系,就能以鸡内金配白术、山药、麦芽,灵活地补虚与通滞并举。这种敢于突破又不失根基的思考方式,使《医学衷中参西录》成为近代中医理论创新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