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后背发凉的,根本不是吴石将军的牺牲。而是几十年后,一个叛徒从资料里推断出的一个结论——在对岸,可能还有两个比吴石级别更高、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谁的“自己人”。 而且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 就说吴石被捕,副官聂曦被捕,俩人被用尽了法子,硬是一个字没吐。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那个推断出有更高级别潜伏者的叛徒,正是当时台湾省工委的负责人蔡孝乾。 他叛变后,为了向国民党当局表忠心,把自己掌握的所有组织线索都交了出去,可在整理吴石生前的情报交接记录时,却发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破绽——有几批标注“绝密”的军事情报,流转路径里没有经过他这个“省工委负责人”的层级,直接从吴石手里送到了一个“未知联络点”,而且对接人署名始终是一个模糊的代号。 蔡孝乾当时就慌了,他比谁都清楚,能让吴石绕开常规联络线直接对接的人,级别绝对不会低于他。 后来他在审讯记录里写:“吴石对那几批情报的重视程度,远超以往,甚至亲自封装、亲自交接,连我想多看一眼都被拒绝。” 正是这个细节,让他断定,在吴石之上,一定还有两个更隐蔽的“关键角色”,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大概率在当时的台湾军政体系里举足轻重——不然不可能有能力接收如此高级别的绝密情报,还能做到不留痕迹。 再回头看吴石和聂曦的硬气,就更让人心里发沉。 1950年3月,吴石被捕后,国民党特务用了各种手段,老虎凳、辣椒水都上了,他的腿被打断,肋骨断了三根,却始终只说“我是中国人,做的是中国人该做的事”。 聂曦比吴石小15岁,当时才32岁,军校毕业的他本有机会在国民党军队里谋个好前程,却选择跟着吴石做潜伏工作。 被捕后,特务拿着他家人的照片威胁,说“只要招供,就能保家人平安”,他却笑着说“我既然敢做,就没怕过连累家人,你们别白费力气”。 俩人被关押了三个多月,从春寒料峭的3月到烈日炎炎的6月,没漏过一个字。 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临刑前还对着大陆的方向敬了个军礼,聂曦则紧紧攥着口袋里那张没来得及寄出去的家书——信里只写了一句话:“此生无悔,盼山河归一。” 现在想来,他们之所以能扛住所有折磨,或许早就知道,自己的牺牲不是终点,还有更重要的“自己人”在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他们多扛一秒,那些隐藏的同志就多一分安全。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台湾解密的部分档案里,也藏着一些指向“未知潜伏者”的线索。比如1949年年底,台湾军方曾突然调整了金门防务部署,可没过几天,大陆这边就精准掌握了新的布防图; 再比如1950年年初,国民党计划对台湾东部的“地下组织”进行大搜捕,可行动前一天,大部分相关人员却突然消失,只留下几个故意暴露的“外围成员”。当时国民党当局怀疑有内鬼,却查来查去都没头绪,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现在再结合蔡孝乾的推断,这些“巧合”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能提前获取防务调整、搜捕计划这类核心情报,还能精准通知相关人员转移,除了比吴石级别更高的潜伏者,没人有这个能力。 而且这两个人一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大概率是当时在台湾军政界能接触到核心决策的人,可能是某一位将领,也可能是某一位行政官员,只是他们把自己藏得太深,深到几十年过去,连档案里都找不到他们的半点痕迹。 有人说,或许这两个人早就完成了任务,选择用普通人的身份过完了一生,至死都没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有人说,他们的档案还锁在某个未解密的仓库里,要等合适的时机才会重见天日。 不管真相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和吴石、聂曦一样,都是抱着“山河归一”的信仰,在黑暗里独行的人。他们没留下名字,没留下事迹,却用自己的方式,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为国家统一默默铺路。 比起有名有姓的牺牲,这些“无名者”的存在更让人震撼。他们不像吴石那样被载入史册,却可能在更关键的位置上,做了更重要的事。 他们让我们知道,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路上,从来不是只有少数人在战斗,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英雄,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心底的信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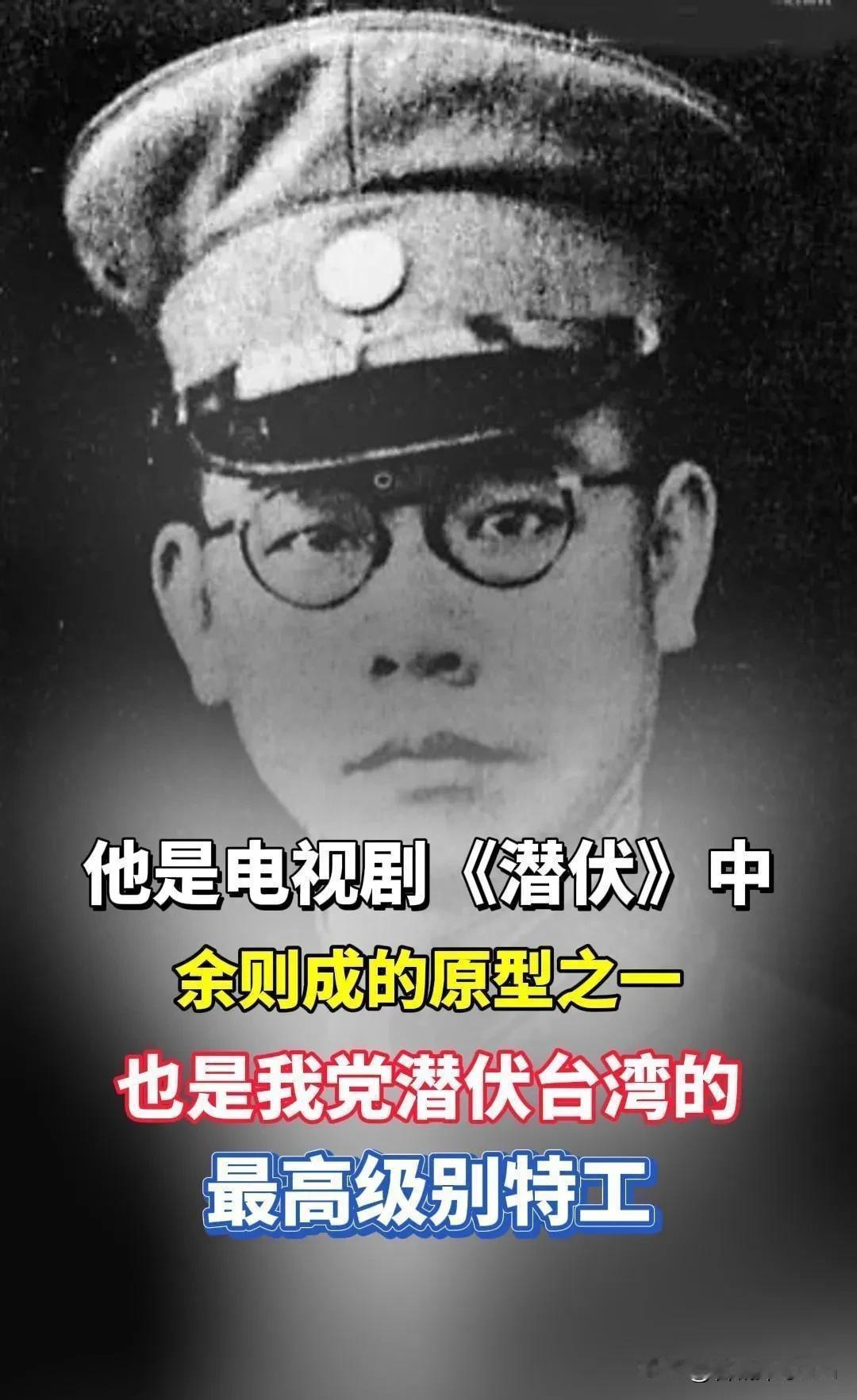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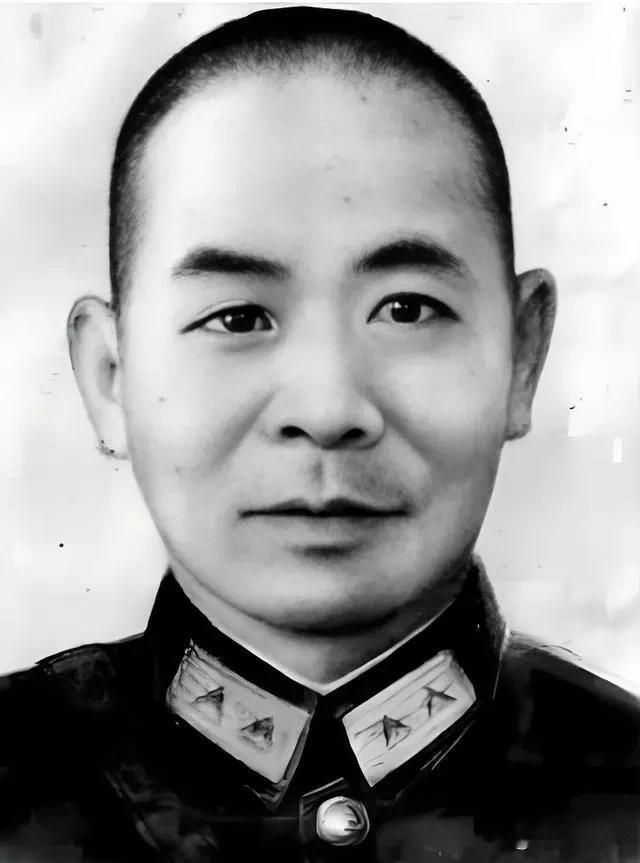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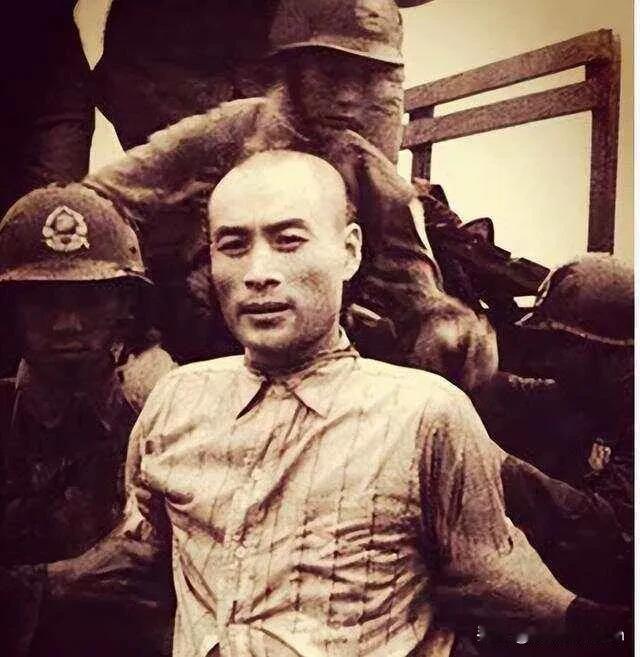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