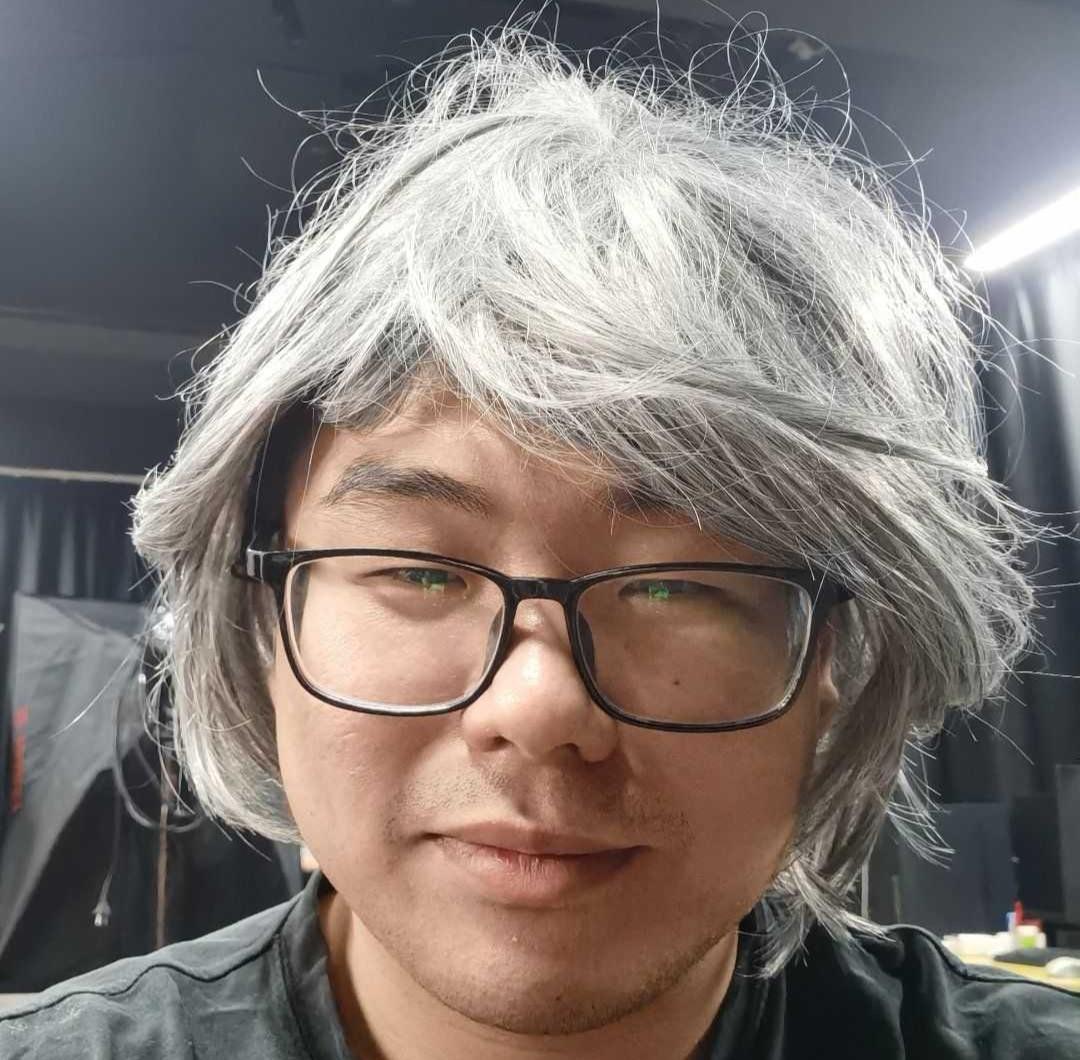本以为杨振宁就是天花板了,没想到的他父亲的身份更是好家伙,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他教过的学生名单拉出来,俩名字就够了:陈省身,华罗庚。 对,就是数学课本上那俩。 提到杨振宁,多数人会立刻想到“诺贝尔物理学奖”“与爱因斯坦比肩”这些标签。 在大众认知里,能在物理界闯到这个份上,早该是一个家族的“巅峰”。 可要是翻开他父亲杨武之的人生档案,才会发现这份“厉害”早有源头。 中国第一位专攻数论的数学博士,亲手撑起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早期框架,就连课本里频繁出现的陈省身、华罗庚,当年都曾坐在他的课堂里听群论课。 这位看似低调的数学家,不仅在近代中国数学史上砸下了第一块基石,更用一辈子的言行,养出了能跨越三代的家族家风。 1923年,安徽有了公费留美名额,27岁的杨武之抱着“把真学问带回来”的念头报了名。 初到美国,他先在斯坦福大学补基础,发现自己对“数论”最感兴趣,又转去芝加哥大学。 那里有当时世界顶尖的数论专家L.E.迪克森,为了跟上进度,他每天泡在图书馆12小时以上,连圣诞节都在啃《数论讲义》。 1928年,他的博士论文《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通过答辩,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靠数论研究拿到数学博士的人。 彼时国内数学界还处在“翻译国外教材”的阶段,他的这篇论文,直接让中国数论研究跟上了国际步伐。 回国后的杨武之,成了“拓荒者”。 1929年他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任教时,系里连一本完整的数论教材都没有。 他干脆把自己在美国用的英、德文专著拆开,每天晚上在书房里逐页翻译,遇到复杂的公式,就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来,第二天带着这些“散装讲义”去上课。 学生们后来回忆,杨老师讲课从不用华丽辞藻,却能把抽象的群论讲成“看得见的规律”,连基础差的学生都能跟上。 更难得的是他的“识才眼”,1931年,他看到一篇署名“华罗庚”的论文,里面对一个数论问题的解法比国外学者更简洁。 后来,他不仅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当助理,还亲自带他读论文,甚至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分给他做。 正是这份提携,让华罗庚从杂货店伙计变成了后来的“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陈省身当年在清华犹豫要不要转几何方向,也是杨武之找他长谈,建议他“去研究能站得住脚的基础理论”,还帮他联系了德国的导师,这才有了后来的“微分几何之父”。 杨武之教学生有魄力,教自己孩子却格外“慢”,这份“慢”里藏着他的教育智慧。 杨振宁不满一岁时,杨武之就赴美留学,家里只剩妻子罗孟华带着孩子。 罗孟华虽没上过新式学堂,却念过私塾,深知“识字是根基”。 她把方块字写在硬纸板上,做成卡片,每天晚上抱着杨振宁认两个字,遇到“山”“水”这样的字,还会指着窗外的景色解释。 就这么坚持了一年多,杨振宁4岁时已经能认3000多个字,能自己读《三国演义》的简写本,这在当时,比很多小学毕业生的识字量还多。 等杨武之回国,发现儿子总喜欢翻自己书架上的数学书,却没急着教他微积分。 相反,他找了清华历史系的高材生丁则良,特意嘱咐,不用教复杂的,就带他读《孟子》,要让他能背下来。 1957年,杨振宁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一时间给父亲打越洋电话报喜。 可这份喜悦,后来却因为“国籍”成了父子间的疙瘩。 杨武之亲历过抗日战争,看着国家在战乱中残破,早就把“报国”刻进了骨子里。 1964年,他听说杨振宁加入了美国籍,气得把手里的茶杯都摔了,给杨振宁写了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失望。 后来父子在日内瓦见面,杨武之提起这事,还是红着眼说,我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就求你别忘了根。 1973年,杨武之去世前,给杨振宁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这两句诗,杨振宁后来裱在书房里,每次看到都忍不住落泪。 其实这份家国情怀,早就在杨家孩子身上扎了根:杨武之的次子杨振汉,西南联大毕业后留美做研究。 后来国内需要先进的物理实验设备,他顶着美国的封锁,偷偷把技术资料复印下来,托人带回国内。 四子杨振平在美国当教授,专门帮国内高校设计实验室,还常带美国学生来中国交流,说“要让他们知道,中国的科研也很厉害”。 2015年,93岁的杨振宁做了个决定,放弃美国籍,恢复中国籍,回到清华大学定居。 现在再看杨武之,“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清华系主任”这些头衔,其实都不是他最珍贵的遗产。 真正厉害的,是他传下来的那份家风:是做学问要踏实的“拙劲”,是心里装着家国的“热劲”,是把知识当成“薪火”的“韧劲”。 杨振宁能成为物理巨擘,不只是因为天赋,更是因为从小被这份家风“养”着,杨家的孩子能各有成就,也因为这份家风早成了他们的“人生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