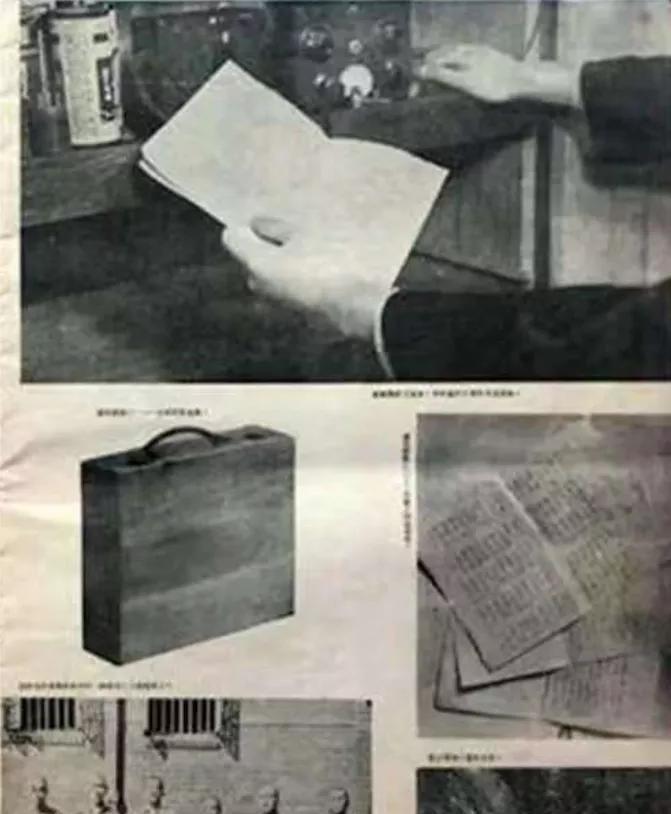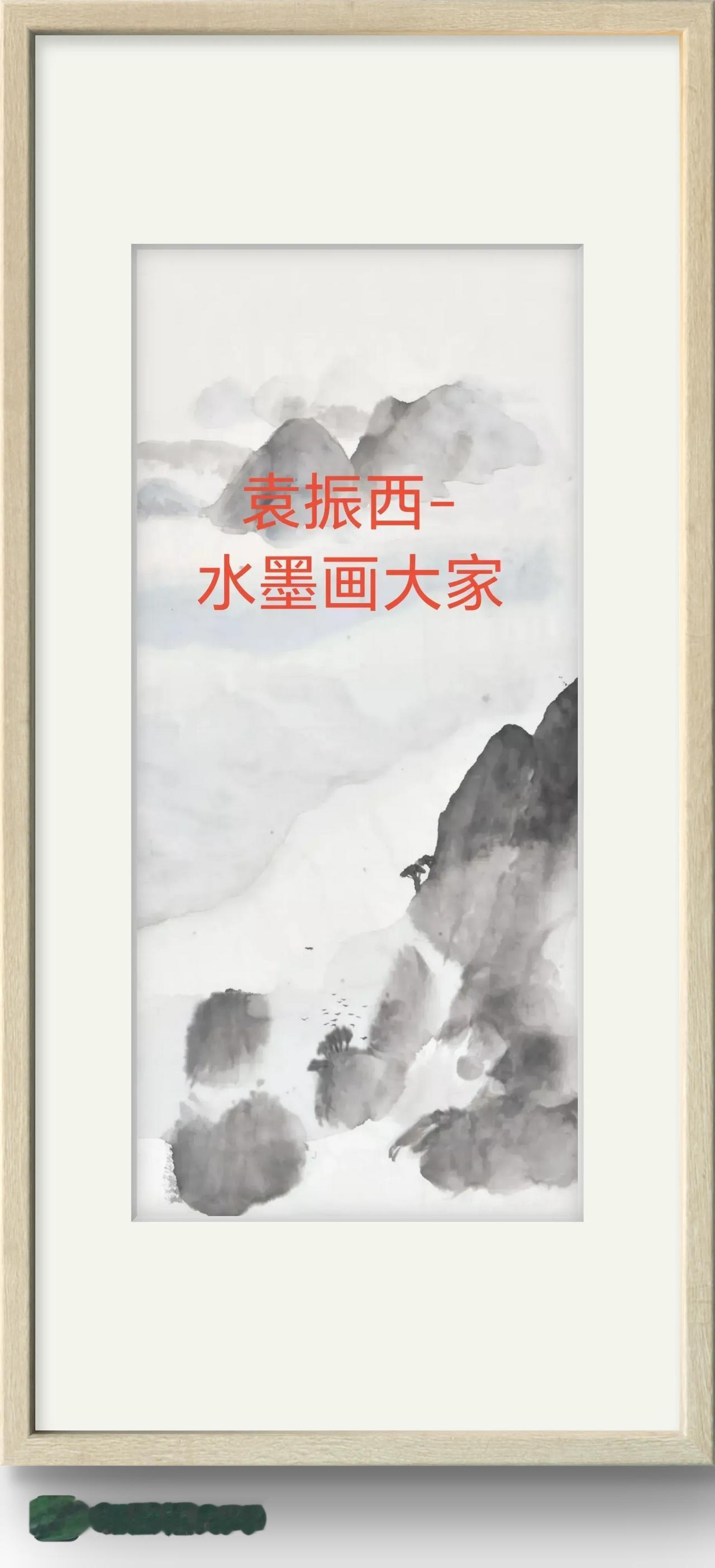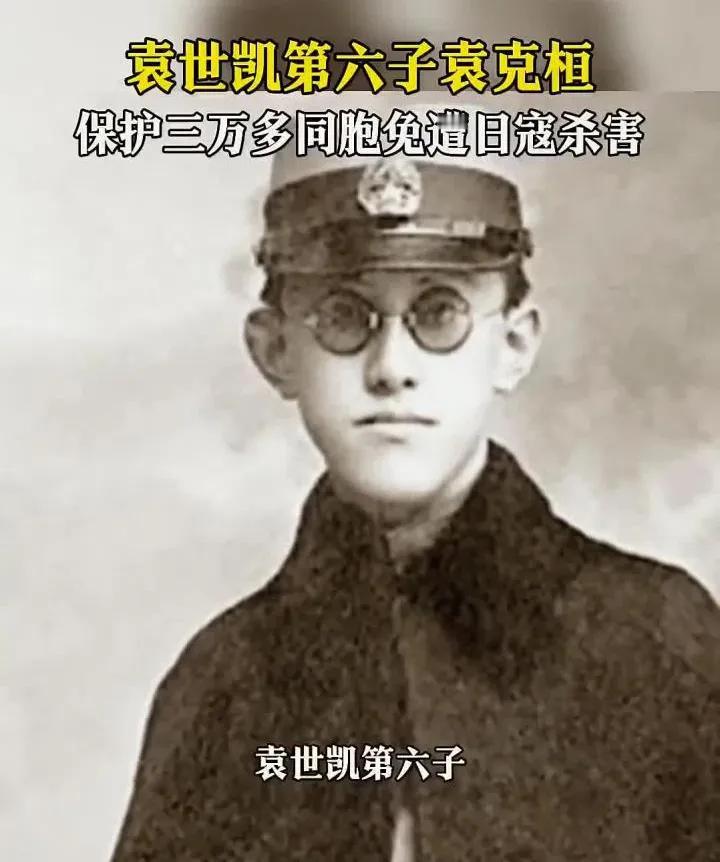1987年,70岁蒋红英买酱油时,偶然看到一张照片,泪流满面:“这是我的丈夫!”
那年夏季的一天,清晨的阳光洒进简陋的小店,蒋红英像往常一样去买日常所需。店主赵桂英,一个外地姑娘,正与邻里闲谈,谈话中“大别山”、“红军”等字眼传入蒋红英耳中,让她手中的酱油瓶骤然沉重起来,那是她心底埋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五十三年前,1928年新县的征兵现场,11岁的她光着脚丫站在队伍里,登记员赵基生的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声响。少年抬头时眉骨的阴影,日后成了她无数次突破封锁线的护身符。他们乔装成夫妻传递情报,赵基生总是把粗粮饼掰成两半,较大的那块总是塞进她的口袋。1932年,在随州的营地,他们的婚礼简单至极,只有几斤炒面作为喜糖,徐向前部队行进的脚步声成了他们婚礼的乐章。赵基生随红二十五军冲锋陷阵时,蒋红英则将情报细细卷起藏在发髻里。双桥镇的胜利消息尚未冷却,三十万国民党军队便如乌云般压境。她在临时医院里最后一次见到丈夫,弹片撕裂了他的肩胛骨,血迹染红了绷带,他将刻有五角星的怀表递给她一半:“等战争结束,拿着这个来找我。”怀表停在了1934年深秋,她吞下情报,大腿被刺刀刺穿,而赵基生则被乡亲们抬往深山。醒来后,部队已踏上长征,而他养伤时却听闻妻子在汉口牺牲。两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战火磨砺成彼此记忆中的烈士。在南京城墙下改嫁的那晚,她将怀表埋入梧桐树下,仿佛埋葬了前半生的所有。小店柜台上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戴着八角帽的方脸男人,正是她的“小赵师傅”。蒋红英指尖轻抚照片,眼眶渐渐泛红,赵桂英吓得打翻了盐罐,她只知道爷爷总是对着旧军装发呆,却不知那件满是补丁的军装里藏着一位名叫“红英”的女子。
在新县的老屋,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82岁的赵基生拄着拐杖站在菜园里,当年挥舞大刀的手如今已无力握住锄头。蒋红英蹲下身,撩起他的裤腿,左小腿上那道弧形的伤疤,是她记忆中他当年摔下山崖留下的痕迹,形状分毫不差。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此刻却像孩子般天真烂漫,一个掏出兜里的炒豆,一个拿出锈迹斑斑的怀表。1994年重阳节,信阳地委大院挂起了“红军夫妻重逢纪念”的红绸,她穿着孙女送的红棉袄,赵基生的军功章闪闪发光。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询问他们是否自愿结婚时,全场哄堂大笑,哪对夫妻需要半个世纪来思考答案呢?婚礼后第七个月,赵基生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他的寿衣口袋里,还装着1932年蒋红英亲手编织的草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