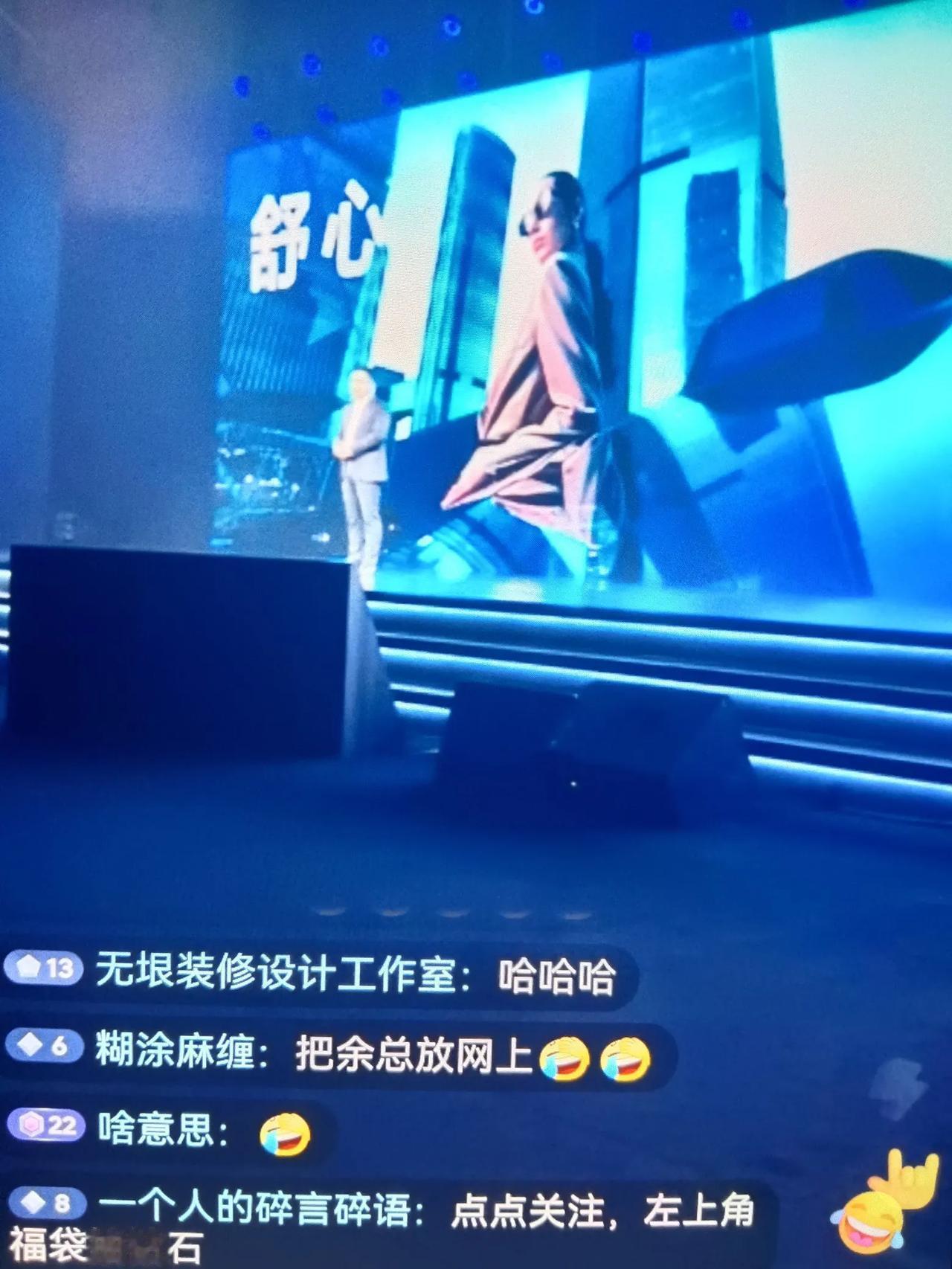1973年,58岁的郑念拒绝出狱,她需要一个道歉,突然,暴跳如雷的监狱长,狠狠地下令说:“把她扔出去…”就这样,郑念被人架着,粗鲁地扔到了大街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郑念出狱那天,天灰蒙蒙的,街头冷清,风卷着尘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她瘦削的身子被两个看守连拖带拽地扔到了监狱门外,膝盖狠狠磕在地上,手掌也擦破了皮,她没有喊疼,只是慢慢爬起来,用手拍掉身上的尘土,理了理乱了的头发,这个动作像她过去每天出门前习惯做的那样,不慌不忙,一丝不苟,她站在门前,回头望了眼那扇紧闭的大门,眼神沉静,却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坚定。 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了许久,这座城市她太熟悉了,曾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失去一切,从一个气质优雅的女外交官、一家外企的总经理,到监狱里的囚犯,她经历了太多太快的转变,可她始终认定,自己没有错。 郑念的确是个不肯低头的人,早年在英国留学时,她就不是那种被规训出来的“淑女”,她喜欢读书,也乐于接触新思想,她曾在伦敦的图书馆里一连坐上十几个小时,只为查一份经济数据,那会儿她已婚,丈夫郑康祺是她在留学时认识的,两人志趣相投,学成回国后一起投身外交工作,后来,丈夫加入了一家跨国石油公司,成为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而她则在背后打理家庭,帮丈夫处理各类事务,是公司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1957年,郑康祺病逝,那年她才42岁,守着15岁的女儿和一摊子事务,没有哭天抢地,只是第二天照样换上整洁的旗袍去上班,她接过丈夫的职位,成为公司新的负责人,在那个女性还很难出头的年代,这样的角色十分罕见,她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员工对她敬重,同行也称她“干练有度”,家里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书籍整整齐齐,墙上挂着几幅字画,角落还有从英国带回来的唱片和茶具。 但这些东西,后来全成了她的“罪证”,1966年夏天,风声渐紧,她出门办事回来,发现家门大开,一群人正在屋里翻箱倒柜,书被撕成碎片,唱片被踩得粉碎,家具也被砸得七零八落,她站在门口,没有喊叫,只是先回了房间,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然后走出去,跟着来人进了看守所。 被关押的那年,她51岁,牢房潮湿狭小,空气里混着霉味和铁锈味,刚进去时,她还以为只要配合审讯,很快就能出来,可几次笔录下来,审讯者根本不听她解释,她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她不再尝试证明什么,也不愿认下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她的方式是坚持一种看似“固执”的生活秩序,她用省下的一点卫生纸糊住墙角的裂缝,用扫帚的尾端蘸水擦洗铁窗,她把牢房收拾得干净整齐,就像她过去照料客厅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身体逐渐虚弱,但她的精神并没有垮,她在心里默默给自己定下目标:活着出去,为自己讨一个说法,她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只能靠回忆撑过每一个漫长的夜晚,她常常想起女儿小时候弹钢琴的模样,也想起她第一次穿旗袍走进学校的背影,她告诉自己,必须坚持下去。 1973年,监狱方面忽然通知她可以出狱,她听完这消息,只说了一句:“要给我一个交代,”这句话让管事的人勃然大怒,当场下令将她架出监狱,那一刻,她知道,不会有人为她所受的苦负责,可她还是不想就这样走掉,她要的不是释放,而是承认冤屈。 回到城市,她第一时间去打听女儿的下落,几番辗转,她才知道,1967年那年,女儿因为母亲被捕而被人揪出来批斗,后来在一次冲突中被打伤,从楼上摔下,不治身亡,官方口径是“自杀”,但左邻右舍都知道,那是被逼的,有人说,孩子被打得几乎认不出样子,摔下楼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张全家福。 这个消息像一把刀子插进她心口,她沉默了整整三天三夜,之后开始四处奔走,她查档案,找证人,写申诉信,到处跑,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不断地追问:“是谁害死了我的女儿?”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找真相,她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让女儿死得明白,最终,她找到了负责当年批斗的人之一,那人被判刑入狱,虽然刑期并不长,但她知道,这已经是她能做的极限。 1978年,看守所正式承认她是被错判,她收到了迟来的“平反”通知书,但并不高兴,公道姗姗来迟,早已无法弥补失去的亲人,1980年,她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生活,她留下了家中所有的古董和字画,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她说,这些东西属于那片土地,不属于她个人。 2009年,她在美国去世,享年94岁,按照她的遗愿,她和丈夫、女儿的骨灰一起被撒进了太平洋,她说,大海会带她们回到黄浦江的尽头,那里有她一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