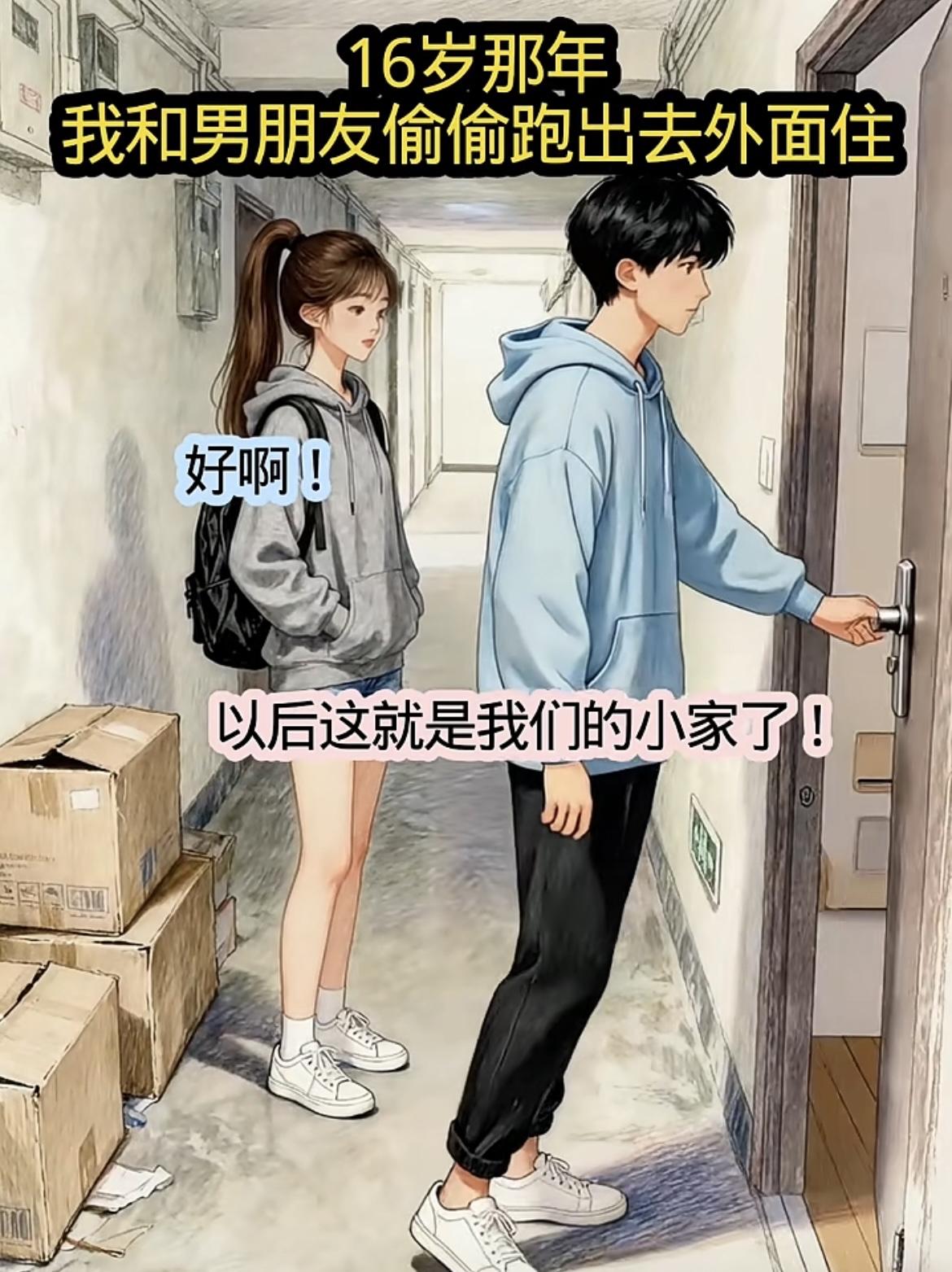打工往事:赵记烧饼,和她消失的老板娘
打工的工业园旁边,裹着一片老城区。红砖墙爬满爬墙虎,电线像乱麻似的架在屋檐之间,拐过第三个堆着废纸箱的巷口,准能闻见一股带着焦香的面味——那是赵记烧饼的招牌香。
我第一次撞见这家店,是入职第一天加班到九点。
肚子饿得直叫,循着香味钻进去,巴掌大的小店挤得满当当,全是穿工装的工友。
柜台后站着个扎马尾的女人,眉眼清秀,手上戴着沾了点面粉的一次性手套,正麻利地往袋子里塞烧饼:“李哥,两个咸香的加辣凉面;王姐,豆沙烧饼要热乎的刚出炉!”
烤炉边的男人背对着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正用长柄铁钳翻着炉里的烧饼。
面团在他手里像有了灵性,揉、擀、撒料、贴炉壁,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等他转身拿烧饼时,我才看清他额角的汗珠,顺着下颌线滴在沾满面粉的围裙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老板河南的?这烧饼味儿够正啊!”我咬了一口刚出炉的咸香烧饼,外皮酥得掉渣,内里带着芝麻的香气,忍不住赞了一句。
扎马尾的女人笑了,眼角弯成月牙:“可不是嘛,俺们老家商丘的,做烧饼传了三代了。”她指了指烤炉边的男人,“那是俺当家的,姓赵。你们叫俺赵嫂子就行。”
往后的日子,我成了赵记烧饼的常客。不是图便宜——一碗凉面加个烧饼才十块钱,够打工人吃个饱嗝——主要是图赵嫂子那股热乎劲儿。
她记性好得惊人,只要来过两回的熟客,不用开口就知道口味。我爱吃咸香加葱花的烧饼,配凉面要多放蒜水少放辣;隔壁工地的李哥每次来都要三个肉馅的,说要给工棚里的兄弟带;写字楼的王姐总赶在下班前过来,打包两个豆沙的,说给上小学的儿子当零食。

赵嫂子的凉面也有讲究,面条是头天晚上煮好过凉水的,筋道不坨。
拌料时先放自家酿的香醋,再淋上炸得金黄的辣椒油,最后撒上黄瓜丝、豆芽和蒜末,香得人直咽口水。
有回我感冒没胃口,赵嫂子特意给我做了碗热乎的鸡蛋面,还加了把青菜,说:“感冒了吃点热的,比凉面舒服。”那碗面没要钱,我硬塞给她5块钱,她追了我半条巷口,最后把钱塞回我兜里:“下次多来吃两回烧饼就行,跟俺客气啥!”
小店虽小,却藏着满满的烟火气。
傍晚时分最热闹,烤炉里的烧饼滋滋冒油,凉面的香气混着工友们的谈笑声飘出巷口。
赵嫂子的女儿放学了,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角落的空桌子上写作业,面前摆着个掉了漆的铅笔盒。小姑娘扎着和赵嫂子一样的马尾,写作业时皱着眉头,跟烤炉边认真翻烧饼的赵老板一模一样。
有回我来得早,看见赵嫂子在给女儿梳头发。小姑娘嫌马尾扎得太紧,噘着嘴撒娇:“妈,你轻点,疼!”
赵嫂子手上的动作放轻了,嘴上却嗔怪着:“扎松了容易散,上学多不方便。”
赵老板端着碗粥走过来,往小姑娘碗里夹了个茶叶蛋:“快吃,吃完写作业,爸晚上给你烤豆沙烧饼。”小姑娘立马笑了,抱着赵老板的胳膊晃了晃:“爸最好了!”

赵老板话不多,却总在细节里藏着温柔。
天热的时候,他会在店门口摆个大水桶,装满凉白开,放几个一次性杯子,供路过的人解渴;下雨的时候,他会把门口的塑料布搭得宽一些,给等烧饼的人遮雨。有回台风天,巷口的大树倒了挡了路,赵老板关了店门,带着几个工友一起去清理,浑身淋得像落汤鸡,回来时赵嫂子给他端了碗姜茶,没说一句埋怨的话,只默默给他擦了擦脸上的雨水。
我们都以为,这家人的小日子会像烤炉里的烧饼一样,越烤越香。直到那年秋天,情况突然变了。
那天我和工友小张下班去吃烧饼,刚拐进巷口就觉得不对劲——往常这个点,赵嫂子的大嗓门早就飘过来了,今天却安安静静的。烤炉还开着,却不见赵老板的身影,柜台后站着个陌生女人,穿着碎花连衣裙,化着浓妆,正低头玩着手机。
“嫂子呢?”我敲了敲柜台,那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语气淡淡的:“谁是你嫂子?赵姐回老家了,我替她看店。”
这时赵老板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个刚揉好的面团,脸色不太好:“媳妇儿家里老人急病,回去照顾了。这是她表妹,过来帮忙几个月。”

我和小张对视一眼,没再多问。点了两碗凉面两个烧饼,那女人慢悠悠地起身拌凉面,调料放得乱七八糟,黄瓜丝没切匀,辣椒油倒多了,吃着又辣又咸。烧饼也是凉的,咬开一口,内里还有点夹生。
“这烧饼不对啊,没烤透。”小张皱着眉头说。那女人翻了个白眼:“要吃就吃,不吃拉倒,刚烤出来的都卖完了。”
赵老板听见了,赶紧走过来,拿起那个夹生的烧饼看了看,又从烤炉里拿出个热乎的递给我们:“不好意思,刚烤的,你们吃这个。”他瞪了那女人一眼,那女人噘着嘴,又低头玩起了手机。
往后的日子,这表妹的操作越来越离谱。她每天穿着不同款式的连衣裙,化着浓妆,跟来打工似的,一点不像帮忙的。赵嫂子以前总穿着方便干活的衣裤,头发扎得紧紧的,而她倒好,头发披散着,时不时就要对着小镜子补妆,桌子上的碗筷堆了半天也不收拾,地上的面粉撒了一地也不管。
最让人不舒服的是收钱的事。赵嫂子以前收钱都规规矩矩放进柜台的抽屉里,每天晚上关店后,会和赵老板一起对账。这表妹倒好,收了钱就往自己的小腰包里塞,有回李哥问她要发票,她翻着白眼说:“小本生意,哪有什么发票?”
有回我亲眼看见,赵老板让她帮忙擦桌子,她扭着腰说:“我这衣服新买的,蹭上油多可惜。”赵老板没吭声,默默拿起抹布擦桌子,额角的汗珠比往常多了不少,却没再让她干活。更奇怪的是,两人说话时的眼神总有些暧昧,表妹说话时会故意往赵老板身上凑,赵老板也不躲,只是低头揉面团。

“你觉不觉得他俩不对劲?”小张偷偷跟我说,“这表妹哪像来帮忙的,倒像个老板娘。”
我点了点头,心里也犯嘀咕。有回赵嫂子的女儿放学过来,看见表妹坐在妈妈平时坐的椅子上,还拿着妈妈的梳子梳头发,小姑娘皱着眉头说:“这是我妈妈的椅子!”表妹瞥了她一眼:“小孩子懂什么,你妈不在,我坐会儿怎么了?”小姑娘吓得眼圈红了,赵老板走过来,没说表妹,只摸了摸女儿的头:“别闹,去里屋写作业。”
那一瞬间,我觉得烤炉里的烧饼香,好像没以前那么浓了。
三个月后,赵嫂子终于回来了。她瘦了不少,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以前总是扎得紧紧的马尾,也松松垮垮地垂在肩上。我特意选了个客人少的时候过去,赵老板刚好去里屋拿东西,我凑到柜台前,小声说:“嫂子,你可得注意着点你那表妹,她和赵哥……”
话没说完,赵嫂子就笑了,只是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妹子,俺知道你好心。可那是俺表妹,从小一起长大的,能有啥事儿?俺当家的不是那样的人。”
我还想再说点什么,赵老板从里屋出来了,看见我们说话,眼神闪了一下,赶紧说:“刚烤好的烧饼,给你装两个热乎的。”

我以为赵嫂子的回来能让一切回到正轨,可没过多久,更糟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我下班去店里,没看见赵老板,只有赵嫂子一个人在柜台后收拾东西,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凉面的调料撒了一地,烤炉是凉的,旁边放着个打包好的行李箱。
“嫂子,赵哥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赵嫂子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哽咽着说:“走了……跟俺表妹走了。”
原来赵嫂子回老家照顾老人的时候,表妹就和赵老板好上了。赵嫂子回来后,表妹不仅不收敛,还故意在她面前和赵老板亲近。赵嫂子跟赵老板吵过闹过,可赵老板铁了心要跟表妹走,说跟赵嫂子过够了这种穷日子,想跟表妹去深圳闯闯。他甚至没提过要带走女儿,只留下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句“对不起”。
“俺们从老家出来的时候,他说要给俺和闺女挣个好前程,可现在……”赵嫂子抹了把眼泪,拿起旁边的书包,“闺女还在学校等俺,俺得去接她。”
那天我没吃凉面,也没吃烧饼,看着赵嫂子抱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心里堵得慌。烤炉里的余温渐渐散了,空气中的烧饼香,也淡了不少。
赵嫂子没关店,她一个人撑起了这家店。可没了赵老板的手艺,烧饼再也做不出以前的味道了——外皮不酥了,内里也没了芝麻的香气。后来她干脆不做烧饼了,改成卖凉拌菜和凉皮,可生意越来越差。以前常来的工友们还会偶尔光顾,不是图味道,只是想帮衬她一把。

有回我去店里,看见赵嫂子在教女儿写作业,小姑娘趴在柜台上,一笔一划地写着“妈妈”两个字。赵嫂子一边给客人拌凉皮,一边时不时看一眼女儿,眼神里满是温柔。“以后打算咋办?”我问她。
她笑了笑,眼里有了点光:“等攒够了钱,就带闺女回老家,开个小超市,陪在老人身边。”
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一年后,当我再次拐进那条巷口时,赵记烧饼的招牌已经不见了,换成了一家卖奶茶的小店。新店主把红砖墙刷成了粉色,烤炉的位置摆了个收银台,以前小姑娘写作业的桌子,变成了客人的座位。我问奶茶店的店员,以前的烧饼店老板去哪了,店员摇了摇头:“不知道,我们接手的时候,店里早就空了。”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赵嫂子和她的女儿。有工友说,看见她们娘俩提着行李箱去了火车站,应该是回老家了;也有人说,赵嫂子去了南方,在一家工厂打工,还带着女儿在附近的学校上学。我宁愿相信后一种说法,相信她能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好日子。
又过了几年,我换了工作,离开了那个工业园,再也没去过那片老城区。有回出差路过附近,我特意拐进那条巷口,奶茶店也换成了一家水果店。我站在曾经的赵记烧饼店门口,仿佛还能闻到那股熟悉的烧饼香,看见赵嫂子扎着马尾的笑脸,听见她喊:“妹子,刚出炉的烧饼,热乎着呢!”
巷口的爬墙虎又长高了,遮住了曾经的红砖墙。来往的行人步履匆匆,没人知道这里曾经有一家烧饼店,有个热情的赵嫂子,有过一段充满烟火气的日子。
我常常想起赵记烧饼的味道,想起那个十块钱就能吃饱的傍晚,想起那家人曾经的欢声笑语。后来我吃过很多地方的烧饼,有装修精致的连锁店,有老字号的百年店铺,可再也没吃过那样的味道——那味道里,有面粉的香气,有芝麻的醇厚,更有普通人对生活的热忱和期盼。
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就像烤炉里的烧饼,火候对了才会香。可赵老板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熄了火,丢了料,把好好的日子烤成了夹生的模样。他以为跟着表妹就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却忘了最珍贵的东西,早就被他丢在了那间小小的烧饼店里。
而赵嫂子,那个被生活辜负的女人,却在熄了火的烤炉边,重新拾掇起柴禾,想为自己和女儿烤出一块热乎的烧饼。她或许没能在那片老城区站稳脚跟,但我相信,凭着那股热乎劲儿,她在哪都能把日子过香。
毕竟,真正能支撑日子的,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闯闯”,而是烤炉里的烟火气,是碗里的凉面香,是家人围坐时的欢声笑语。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和坚守,才是生活最本真的味道。就像赵嫂子的烧饼,外皮再酥,内里再香,少了那份热乎劲儿,也终究成了过眼云烟。
如今再想起那片老城区,我总觉得,那股烧饼香并没有真正散去。它藏在巷口的风里,藏在打工人的记忆里,也藏在每个对生活充满热忱的人心里。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份味道,记得那个扎马尾的赵嫂子,那间小小的烧饼店,就永远不会消失。
听说关注我的人都暴富了~
创作不易!!!对于以上内容有什么看法和想法,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我是贤东,期待与您的交流~(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