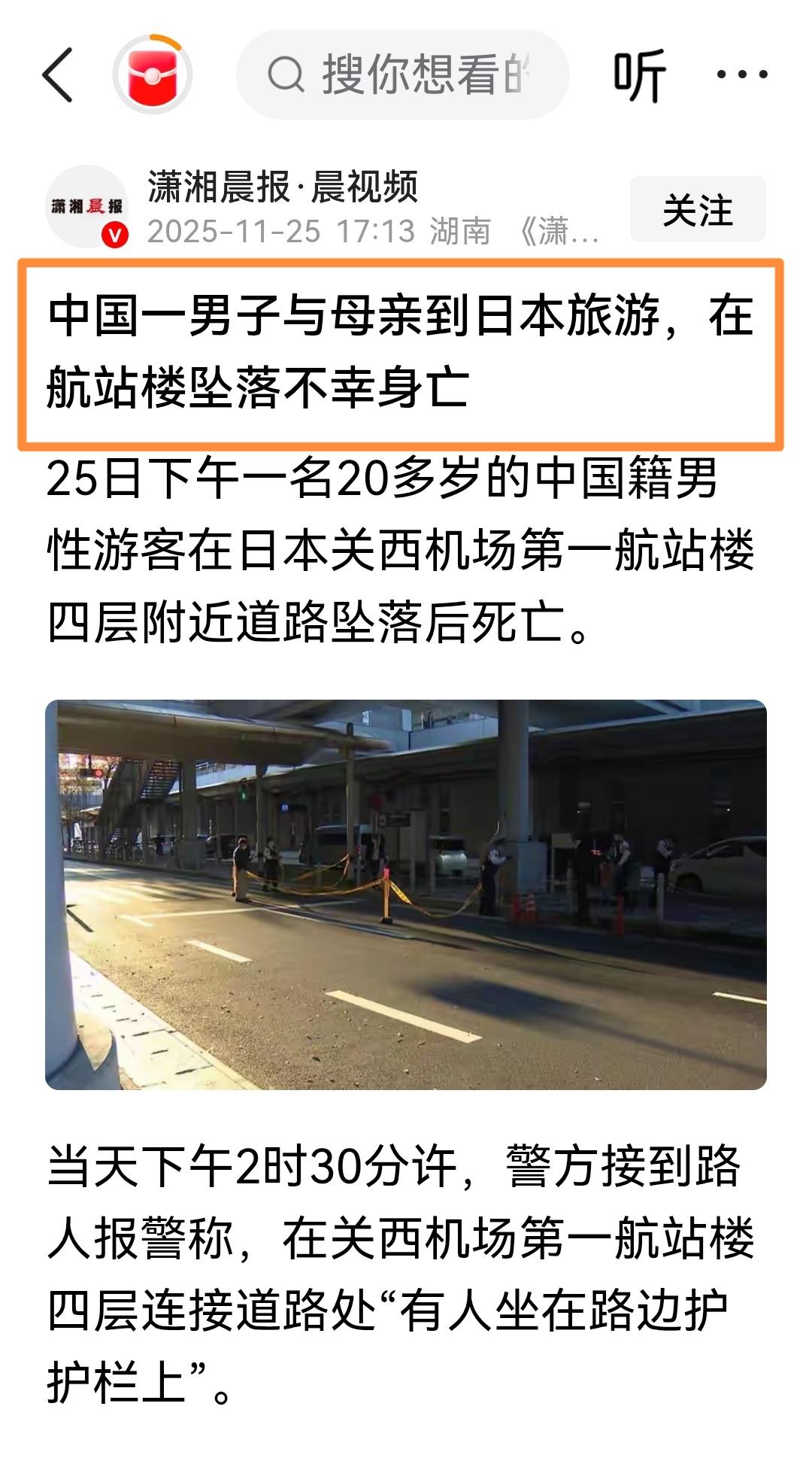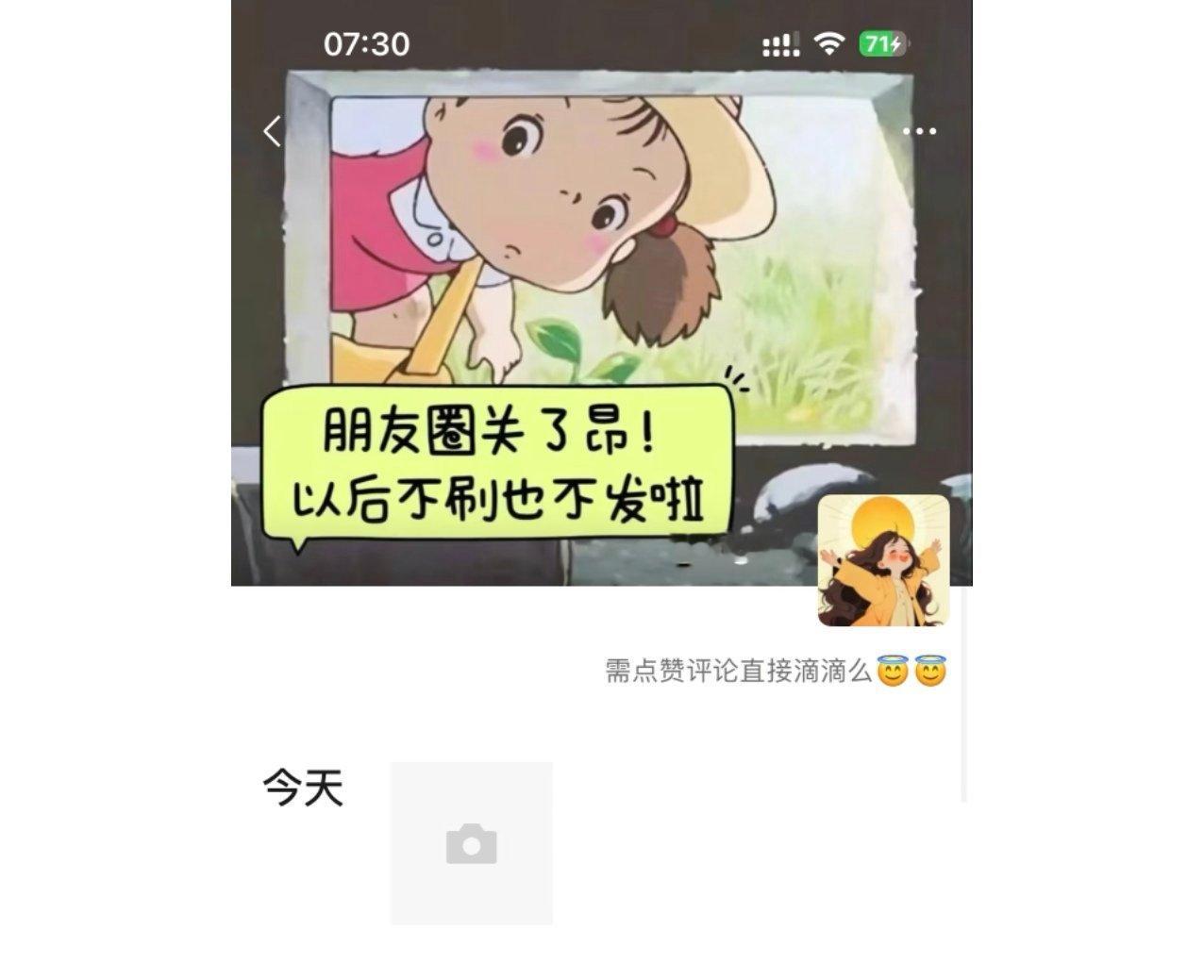作者 | 郭鸿云
编辑 | Sette
当一支由400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在千年古城奏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台下坐着的不仅有古典乐迷,还有被邀请来的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和一线工人。
任谁听到这样的画面描述,都会感到一丝认知错位。然而,这一幕却在盐官“潮乐之城”的潮城艺术中心真实上演。
其中领衔的,正是景区自行组建的国内首支古镇职业交响乐团——嘉兴大潮爱乐乐团。当这场首演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圆满落幕,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音乐不应是高悬于殿堂之上,而应是一种普世的、无门槛的审美体验。
而这一举动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有一个古镇正以音乐为“武器”,进行一场关乎中国古镇生死突围的“实验”。在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内卷”中,试图以独特的主题与内容创新运营杀出重围。

提起中国的古镇旅游,早已是“吐槽”声一片。
昔日的历史文化符号,如今却充斥着相同的臭豆腐、相似的奶茶店、雷同的义乌小商品和千篇一律的汉服写真。
游客的游览体验,也从“发现独特文化”沦为了“在相似布景中完成标准化的打卡动作”。
这种同质化竞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利润摊薄与游客消费欲望的归零。

而盐官潮乐之城以一场中国交响史上超大规模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演出,为古镇创新体验打开了另一种可能:让流动的音符与潮声相和,与江风共舞,将古典音乐的悠扬嵌入千年古城的肌理。
为何一个古镇会想到要做交响乐?盐官古城潮乐之城副总裁鲍龙在接受闻旅采访时提到,这是结合古镇在地文化及地理位置优势的融合创新之举。
盐官作为千年古城,倚靠钱塘江畔,自古以来就是观潮胜地。每月农历初一至初六、十五至二十的大潮期,游客至此既能目睹气势磅礴的潮头奔涌,入夜后,还能聆听声似千军万马列阵而过的轰鸣。

正是这潮声与跌宕起伏的音符间的异曲同工,让顶度集团董事长、乌镇旅游创始人陈向宏及其团队在策划时,萌生了将音乐、潮文化与盐官千年历史相融合的构想。
他们为这座小镇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蓝图:组建一支职业交响乐团,打造一个“全领域音乐生态”。
于是,嘉兴大潮爱乐乐团应运而生。
这支由陈向宏和首席指挥俞潞向全球艺术家发出招募令,从上千位报名者中甄选出的40多名音乐人组成的乐团,平均年龄仅25岁。选拔标准明确而纯粹:技术与艺术素养必须过硬,且怀揣一份真正的热爱。
由于其诞生的特殊背景与肩负的独特使命,这支乐团注定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天团。更重要的是,它要探索音乐与大众旅游的结合之路,实践“古镇+音乐”的新模式,为古镇焕新基因,开创更广阔的天地。
2当然,要打造一个受大众喜爱的音乐小镇,仅靠一支专业交响乐团还远远不够。为何要做此事,又为何是此刻?

鲍龙解释道,在音乐领域,古典音乐代表着最高端的水准。要打造一个立得住的音乐小镇,这座金字塔的“塔尖”必不可少。若能以震撼的交响乐证明专业能力,那么在更广阔的音乐领域,盐官潮乐之城的专业可靠性也将得以确立。
而且古典音乐也在不断演进,趋于年轻化。正襟危坐、庄严肃穆是它,结合在地文化变得灵动亲民也是它。未来,除了演奏经典曲目,嘉兴大潮爱乐乐团也会排演更具本地文化特色的节目,以增强观众的体验感。

更重要的是,盐官潮乐之城并非只有交响乐。早在举办这场震撼音乐会之前,此地已举办过多场更大众化的流行音乐会,并与太合麦田、腾讯音乐等知名品牌展开合作。
这些音乐节在游客中反响良好。加之景区内的街头音乐表演、KTV活动,将话筒交给观众以增强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共同构成了支撑这座音乐小镇更稳固的“塔身”与“底座”。

官方统计显示,从去年9月开园运营至今,盐官潮乐之城接待游客量已超200万人次,超出了项目预期目标。
这一模式并非引进几家网红店铺、举办几场音乐节就能轻易复制的。从运营角度看,它不仅需要强大的资源链接能力、对音乐领域的深入了解与渗透力,更须具备长期供养大批音乐人才、持续投入资金的能力。
仅看一点:爱乐汇文化公司董事长、爱乐汇交响乐团团长宋建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供养一支职业交响乐团,保守估计年花费在千万元以上。这不是一般文旅项目敢跟、能跟的。这本身,就是最硬的竞争壁垒。
这也使得运营方对盐官潮乐之城的期待,远不止于提升游客体验、带来视听享受,并非举办一两场音乐会或演唱会就能满足。
鲍龙坦言,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知名的音乐“乌托邦”和度假胜地。
3乍听这一宏伟目标,不免让人联想到乌镇。
同样由陈向宏一手打造,如今的乌镇戏剧节已享誉海内外。自2013年首届举办至今,这个节日IP不仅重塑了乌镇这座千年古镇的内涵与经济生态,更成为全球戏剧艺术家与年轻创作者的心灵归属地。
而盐官潮乐之城,不仅在愿景上与乌镇有相通之处,在生态构建的路径上也异曲同工。

例如,这里已发布“音乐人驻留计划”,不仅与政府合作,为来到盐官的优秀音乐人提供扶持政策,鼓励其在此创作发表歌曲,还为年轻创作者或暂时面临资金困难的音乐人提供免费食宿,支持其独立创作。
据鲍龙介绍,该计划推行至今,已吸引近百位独立音乐人来到盐官,或常驻,或短暂停留。他们都曾在此留下跳动的音符,为游客带来难忘的音乐盛宴。
“盐官潮乐之城就是一个平台,为全国乃至全球怀揣音乐梦想的人提供聚集地、实现梦想的舞台、找到伙伴的阵地,以及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空间,亦可称之为乌托邦。他们既丰富了游客体验,为古镇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内容,也在这片‘沃土’上成就自我。这才是让古镇得以持续健康运营并更好发展的生态模式。”

另据闻旅了解,未来两年,这座千年古城还将孕育一个全新、不同于以往的音乐节IP。正如当年的“乌镇戏剧节”,这个音乐节,亦有望成为每一位音乐爱好者的“朝圣地”。对此,我们报以期待。
纵观盐官潮乐之城这个项目,其本质已从“运营一个景区”升级为“培育一个产业生态”。其策略是“去古镇化”,目光更为高远,但面临的挑战也必然倍增。
首当其冲的便是内容的持续力——能否如愿吸引音乐人不断奔赴,并持续产出高质量、有吸引力的内容,而非仅依赖硬件投入。其次是产业融合度——能否真正吸引头部音乐平台与机构落户,形成资源闭环,而非仅作为旅游观光的“背景板”。

更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元素与专业团队的加入,究竟能为景区增值多少?除门票收入外,如何有效赋能并联动更多周边消费可能性?当这一模式日趋成熟、接近目标时,这些问题必将成为业界关注与探讨的焦点。
但无论如何,盐官潮乐之城的尝试,无疑为困境中的古镇文旅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
它大胆地提出:古镇的底色可以是历史,但它的未来未必只能被历史框定。在保留文化底蕴的同时,完全能够植入最当代、最具活力的内容产业。
这是一场“音乐实验”,更是一场以在地文化创新为底气的“豪赌”。
若成功,盐官将不再仅是一个“观潮胜地”,更将成为一个“听乐新城”。同时,也为无数“千镇一面”的古镇们蹚出了一条突围新路径:找到属于自己那份独特而可持续的“内容之魂”,远比修复一千座古建筑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