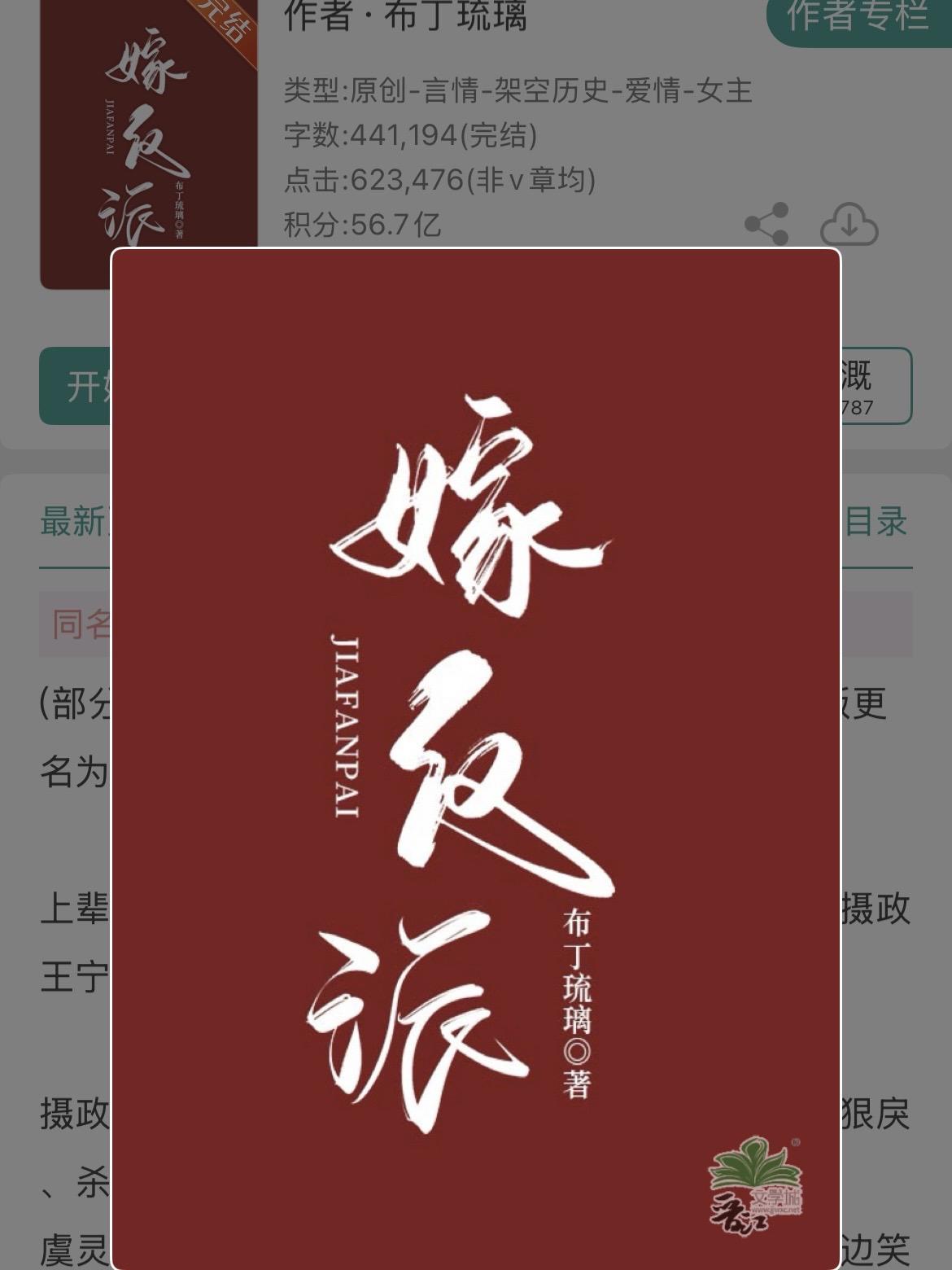我成婚的那天,竹马踉踉跄跄闯进来,要抢亲。
他两眼泛红盯着我一身喜服:
“你不要我了吗?”
面色惨白,仿佛痛失所爱。
就好像,少年时面目狰狞地说宁死都不娶我的人,不是他一样。
一
“谁要娶那个老女人!”
少年摔了酒杯,门外送汤的我被吓了一跳。
有人笑道:
“那李家姑娘虽长你两岁,今年也才十七。怎么都谈不上老吧?”
“就是,听说还是个小美人呢。”
少年冷笑一声:
“上京的美人都死绝了?一个杀猪户出身的,也称得上美人?”
他灌下一口酒:
“凭什么我就得娶了她,还一辈子不能纳妾?就凭她爹救了我爹?
“这偌大的恩情,我爹不若自己还,自己娶了她去!”
这样议论长辈,就有些大逆不道了。旁的世家子弟没敢接茬。
他却是个来疯,旁人越是战战兢兢,他越是得意发狠:
“强买强卖是吧?少爷我偏就不吃这套!
“她敢嫁,我就敢给她吃不完的苦头!”
我在门外沉默半晌,拎着食盒走开了。
干娘让我来给他送醒酒汤,是怕他喝多了耍酒疯,也让我盯着他早些回家。
可我眼下要是进去,怕是火上浇油。
跟着我的小丫鬟看不下去,小声道:
“小姐,少爷一贯这个脾气,只是不喜老爷夫人拘着他,不是真的嫌弃小姐……”
“没关系,”我笑笑,“我明日会同干爹干娘说,不要这样强迫他了。”
我做女儿孝敬他们一世,也一样的。
可我没想到,第二天,我才同干娘开了口,干娘就命人将宿醉的他从房里拖了出来,直接请了家法。
两掌厚的板子抽在他身上,干娘怒骂:
“成曜,你还有没有良心!”
少爷——不,成曜盯着我,满眼都是恨意。
二
我惶惶去拦。
“干娘,别打他!”我说,“他没有做错什么——是我,是我不想嫁!”
闻言,干娘和成曜都愣住了。
干娘怔怔地:“乔乔,你、你不想嫁?你不是……从小就喜欢他吗……”
成曜直接甩开了压着他的家丁。
他从凳子上立起来,盯着我,双眼阴沉沉的:“你再说一遍?”
“我不想嫁给你,”我慢慢地说,“我想嫁个一心一意喜欢我的人。”
我对干娘道:
“我知道,干爹和干娘,是念着我爹救过干爹的命,所以总想着补偿我……可成家自九岁起养我至今,再大的恩也还清了。”
“这怎么还得清?”干娘打断我。
她抡起板子抽向成曜:“这孽障狼心狗肺,我打服了他!”
我拦不住干娘,也劝不住她。
干娘只说:“乔乔,你别犯傻。你嫁给他,他若敢待你不好,我和干爹还能帮你揍他。”
“你若嫁给旁人……这上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都是早早定亲的,你如今十七了,匆匆忙忙,到哪里去找像样的夫家?”
“可你若嫁得不像样……我和老成到九泉之下,怎么见你爹?”
我说什么都不管用。
干娘发了狠地打着成曜,边打边哭。
偏偏成曜也犯了倔,咬着牙一声不吭。
那一场家法,打得成曜在床上趴了半个月,更恨我了。
我去送药,去看他,都被他轰了出来。
“你得意了,来看我笑话?”他厉声道,“李乔,我们走着瞧!”
半月后,成曜能下地了。
——离家出走了。
出走前留了字条:“宁作逍遥士,不娶无盐女。”
一度成为上京纨绔中的美谈。
他们笑赞他是真豪杰,无人在意,好好一个姑娘,就这么被他说成了“无盐女”。
三
干娘日日以泪洗面。
她似乎是怕我心灰,拉着我一直劝:
“他还没长到懂事的年纪,你比他大些,等等他好不好?”
“他会懂事的,等他大了,就知道谁真心待他好。”
我咬着唇,不答腔,只说:
“干娘,我们得尽快把他找回来。”
将军府独子离家出走,不是什么风光事情。
干娘道:“乔乔,你去,你能把他找回来。”
我一愣:“我?”
我怎么找?
“你能的,乔乔,你忘了?那混账小时候也犯浑躲起来,我们谁都找不着他,只有你能。”
可那是小时候。
小时候的成曜,不是如今这样子的。
那时他最喜欢我,去哪都要追着我跑。
而如今他一见我就满目嫌恶,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
“乔乔,你和他一起长大,是这世上最了解他的人,”干娘哭道,“你去找找他,好不好?干娘求你了。”
我看着干娘泪流满面,哭得几乎背过气,到底垂下眼:
“我试试。”
我还真的找到了他。
烟花柳巷,靡音阵阵。
上京最风光的歌妓,一曲过后,台上打赏的金银零碎不计其数。
其中一只镯子尤为扎眼。
我认得那镯子。
通体白糯,润如羊脂,是西域那边的物什。
那是我生父从军后第一次出征,带回来给我母亲的。
——成曜从家里偷出去、打赏歌妓的,是我母亲最宝贝的遗物。
四
我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了成曜。
他坐在高处,醉眼迷离地笑着看台上的歌妓。
猝不及防,他面前出现一个我。
他散漫的神色,一下子冷了下来。
“滚开,”他冷冷道,“真会坏人兴致。”
“拿回来。”我说。
“你扔到台子上的,是我娘的遗物,”我咬着牙道,“你偷我旁的金钗银镯便罢了,我娘留给我的东西,你也偷?”
盛怒之下我声音都发颤,眼中也盈了泪。
有人循声看过来。
成曜觉得没脸,梗着脖子道:
“我偷你的东西?你从小吃我家的喝我家的,成府哪有你的东西!”
“不就一个破镯子!权当抵了你在我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
我握紧了拳,指甲掐进手心。
“养我的是干爹干娘,轮不到你说这种话,”我一字一顿,“拿、回、来。”
“我就不,”他的唇角恶意勾起,“有本事,你自己去台上捡回来。”
我没有犹豫,转过身就爬上了台。
伸手一勾,将那只镯子牢牢攥在了掌心。
看客们没想到有这一出,纷纷叫骂。
“这人干什么的!”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这地方自然有打手。
几个面相凶恶的大汉快步向我扑过来。
我心中一慌,下意识去看成曜。
他抱着臂,一脸看好戏的神情,还带这些大仇得报的快意。
我心中一紧。眼见那几个彪形大汉就要扑向我,情急之下厉声道:
“此乃烈士遗物!”
“引来官府查抄,你们这地方不想开了?”
声色凌厉,竟真唬住了他们。
场面僵持,而我只死死盯着座上的成曜。
无数人的目光随我一起看向他。
成曜脸上阵红阵白,咬牙切齿——那个表情我看得懂,他在说“真丢人”。
他咬着牙,近乎是落荒而逃。
而我对着楼中人一礼:
“既是少爷赏姑娘的,府上稍后会将等量银钱奉上。叨扰了,抱歉。”
我礼数周全地出了楼。
才过拐角,便被人一把扣住脖颈。
五
成曜气得手直发抖,眼中发狠:
“敢给少爷我没脸?”
我盯着他,泠泠道:
“你每次溜出去玩乐,从干娘那里要不到钱,就去我房里偷我的钗环去当掉。——我真想给你没脸,早就把这件事捅到干爹干娘那里了。”
“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我说,“我只是不想干爹干娘生气。”
首饰而已,少几件就少几件罢。
总好过看干娘气得心口疼,把成曜打一顿,回头成曜又想些幺蛾子来整我。
我说:“但我娘的遗物不行。这时她留给我的,我要戴着出嫁的。”
成曜睨着眼看我:“出嫁了也是我的。”
我愣了愣,然后一字一顿道:“不是。我不嫁你。”
娘和干娘都说,嫁娶之事关乎女子的一生。
而今成曜种种行径,更是让我坚定——我怎能将一生,托付给这样一个人?
“轮得到你说嫁不嫁?”成曜嗤笑一声,“你当我就想娶你吗?!要不是父母之命——”
“干爹干娘那边,我会想办法。不劳你费心勉强。
“只是往后,也请成少爷不要再打着我未婚夫的名义,对我百般挑剔嫌恶——我没道理受这般羞辱。”
他脸色青白怔在原地,半晌后忽然冷笑一声,带着些咬牙切齿:
“好,好得很!”
他忽地一把掳过我,不知从哪里抢了匹马。
马匹一路狂奔到城郊,周遭愈发破败荒凉。
我慌了:“成曜!你来这里做什么!”
城西偏僻,三教九流混杂。官兵都管不住。
据说这里还藏了个土匪窝。
成曜面露得色:“怕了?刚刚教训我的劲头呢?”
他将我一把从马上推了下去。
我毫无防备,猝不及防在地上滚了几滚。
抬起头来时,便见他已调转马头扬长而去,全然不顾我的呼喊。
只背对着我丢下一句话,大笑声里藏不住得意:
“我看你才是欠些教训,有本事就去找我娘告状——就怕你找不回去!”
六
我留在原地,恐惧后知后觉地漫上来。
夜幕浓稠,远处传来打更声。
二更了。
此处远离城中灯火,只有月光,我几乎无法视物。
喉间阵阵发紧。我低头抹了一把脸,佯作平静地沿来时路往回走。
往东,一路往东。只要走进灯市繁华处——
我拐进一条巷子。
逼仄的小巷正有个男人出来,像是要在路边小解。
他一抬头看到我,咧嘴笑了。
露出一口暗黄的牙。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快步就要出去。
快了,就快了,只要几步——
“呦,小娘们儿,躲什么啊?”
那人轻易便追上了我,一把捂了我的嘴。
扑面而来的臭气和酒气。
他将我压在墙上,嘿嘿地笑:“多久没碰过女人了……正好给我解解馋……”
他压着我,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慌极了,咬牙用力得脏腑都要出血,却推不开。
他脏污的手扳过我的脸,看清之后,却僵了僵。
天人交战半晌后,他咬牙啐了一口:
“娘的……这么好的品相,得老大先弄。”
他绑了我,用一团布塞了我的嘴,将我拖到了一个小房子。
那人将我向门里一丢,锁上了门。
我借着昏暗月光看了一眼,发现此处竟有不少被关押的人。
男女老少皆有,神情木然,像在等死。
——此处,还真是个如假包换的匪窝。
七
“新抓的这个,什么来头?”门外有人粗生粗气道。
“管她什么来头!”抓我那人道,“能走到这里的小娘们儿,八成是自己偷跑出来的,等老大玩够了,我们一起玩,再找地儿埋了就是——谅她娘家夫家也没脸找她。”
我咬紧了唇,牙齿止不住打战。
我想起许多年前,世道乱,山匪屠城,专杀朝廷官员。
那时的成曜还是个小孩子。
干娘带着他和我躲在地窖里,他看着我和干娘泪流满面,挺起了小小的身体,将我们护在身后。
“娘别怕,乔姐姐别怕,阿曜保护你们!”
许多年后。
那个信誓旦旦说着要保护我的少年,因为我折了他的面子,亲手将我丢进了土匪窝,扬长而去。
他为一时之气,将我丢进了……被糟蹋然后埋尸荒野的命运。
我咬紧了牙关,忍住眼泪,开始打量起这间小房子里面的人质。
逡巡过后,我艰难地一步一蹭,挪到一个男人身边。
他微微偏了偏头,耳朵向着我的方向。
——这男人是个瞎子。
我唔了几声。
他怔了怔,道一声“得罪”,然后伸出手,指尖擦过我的发丝,略略迟疑,拿掉了我嘴里的破布。
还不等他开口,我就道:
“你家里会有人来赎你,是不是?”
八
男人一怔:“你怎么知道?”
他衣着普通,却生了双养尊处优的手。
虎口和指节都没有茧,不是文人也不是武人……就不是个干活的人。
这是个被人侍奉的主子。
我说:“等你家里人把你赎走,能不能帮忙向我家里带个信?我不想……我想埋在我爹娘身边。”
我尽力让唇齿清楚,却开始控制不住牙齿格格打战。
我很怕,怕极了。
就在这时,门外却隐隐骚乱起来。
“走水了!”
原本在门外说话的两个匪徒,似乎是向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跑去。
我心念一动。
此处茅屋的柱子有些开裂,我用木刺割断了手腕上绑的布条。
然后开始给身边的人松绑。
有人战战兢兢道:“没用的……有人看着我们……”
我咬了牙,一脚踹在门上。
门上了锁,踹不开,可是门外竟也没有呵斥的动静。
“他们走了!”我说,“应该是去救火。我们要么趁乱逃,要么在这里被活活烧死!”
人质们开始恐慌躁动起来。
有人跟着我一起撞门,撞开之后,扑面而来的是滚滚热浪。
只是这动静也让匪徒们听到了。
有人尖声道:“他们要逃!”
男女老幼的人质,像洪流中涌出的乱兽,四散奔逃。
逃跑前最后一眼,我看到了那个男人。
大抵是因为目不能视,他怔怔站在人群中间,似乎不知该逃往何处。
九
我一咬牙,只犹豫了不到一瞬,回身将他拉起来:“跟我走!”
我抢了一匹匪徒的马,载着我和那个男人狂奔。
匪徒们追杀的声音响在背后。
我不敢回头看。满心战栗,只怕自己血溅当场。
就是这样混乱的当口,我却听到清脆一声响。
镯子掉了。
温润的羊脂白玉,就这样从我的袖袋滑落,滚进了一地黑泥。
我头都没回。
咬着牙,一路骑马狂奔。
那男人突然道:“你哭了。”
他说:“小姑娘,你很害怕吗?”
“我的宝贝,”我一张嘴,果然带了哭腔,“我最宝贝的宝贝,丢了!”
话虽如此,策马却一步不敢停。
再珍贵的物件和念想,都没有活着重要。
这一路太恐慌,太凶险。我不记得自己跑了多久。
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弃马脱身,怎样把瞎子安顿好,又是怎样一个人爬回的府。
我想我一定形容狼狈。
因为街坊们见到我的时候,都在窃窃私语。
“像什么样子!”
“这,这成何体统!”
干娘亲自将我拎回了府,关上大门,隔绝那些窥视的目光。
“说吧,怎么回事。”
我一抬头,却看到了成曜。
他抱着手臂,事不关己地靠着墙,嘴角邪邪勾起。
那眼神是在说“算你走运”。
而我与他对视半晌,分明有漫天恨意翻涌,却觉得全身气力都被抽尽了。
我缓缓跪伏下去,像一滩烂泥一样,铺在了堂屋的青砖上。
“我会交回庚帖婚书,也请干娘把我的庚帖给我,婚事作罢——否则,请干娘准我死个痛快。”
十
干娘惊慌地来拉我:“乔乔,你别糊涂——”
我说:
“我永远是干爹干娘的女儿,但绝不会做成家的儿媳,成曜的妻。
“求干娘成全——阿乔愿以死明志!”
我向干娘深深跪伏。
干娘沉默良久,动作僵住。
半晌后,她似乎是冷笑一声。
脸色也冷下来。
“好,我也只能依你,”良久之后,她说,“现在你可以说了——你做什么去了?怎么弄成这副样子?”
她与我,似乎霎时生分了下来。
仿佛又变回了年少时,我躲在母亲身后看到的,那个矜持尊贵的将军夫人。
我觉得心口一寸寸凉下去。
“成曜将我丢进了土匪窝,”我神情木然道,“那些匪徒决定奸杀我……好在匪窝里失火,我趁乱跑出来了。”
哐当。
我没来得及看干娘的表情。
因为成曜捏碎了手里把玩的白玉杯,脸色玩世不恭的神色褪去,惨白得像一张纸。
他哑声道:“你再说一遍——他们,那些人,把你怎么了?”
十一
我与成曜的婚事,本该是桩美谈。
世人谁不赞叹成老将军有情有义,而我命好,土鸡飞上枝头。
明明是两家都欢喜的好事,我却不识好歹执意退亲,甚至以死相逼。
“她也忒不知足,心气太高了吧,还想嫁谁?”
“成家养她这么多年,谁承想,养了个贪心不足的白眼狼!”
上京的贵女夫人们,纷纷为干娘不值,见我时,都恨不得替干娘教训教训我。
干娘只笑着打圆场。
私下里,劝我不要争辩。
“干娘知道,你受委屈了,”她悄声道,“可被掳进匪窝,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名声不好的。还不如她们说你忘恩负义……认了吧。”
我觉得委屈,胸中像堵了金块,咽不下呕不出。
从我拒绝嫁给成曜之后,成家上下都对我淡淡的。
所有人虽不明说,可满眼都写着——“你什么时候走。”
只有成曜,不依不饶地来找我。
他问我:“他们伤你没有?那些山匪……他们,把你、那个了没有?”
他的眼睛盯着我,眼底血红。
目光像带血的钩子。
我没理他。关上了门,任由他在门外发疯砸东西。
干娘开始借着各场赏花茶会为我相看。
她不可谓不尽心。
可在我避开各类纨绔鳏夫淫邪挑剔的目光,低头沉默之后。
干娘没了耐心,神情淡淡地敲打我:
“你毕竟年纪大了,相看时不好心气太高。”
我想,我年纪大了吗。
可为什么无数次长夜噩梦中惊醒时,我还是下意识想找娘。
可我娘不在了,家也不在了,唯一的念想都丢了。
我抿紧唇垂头,红了眼眶,听到干娘不耐烦地啧了一声。
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花会的主人听了下人来报,面色一变。
贵女夫人们纷纷拎着华丽裙摆跪了下去,神情恭敬紧绷,仿佛迎神。
一个小小的赏花会,竟能有宫里的人来传信。
公公吊着嗓子,语气矜持:
“哪位是李家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