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心果和疫苗汤
文、图 赋格
续接第一篇 《城市化为乌有》 。
01
赖床之际,在手机上翻找《纽约时报》近年有关加济安泰普的文章,先注意到一幅插画:最近这次土耳其大选中各地支持埃尔多安与支持反对党的区域分布图。黄区代表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胜出的区域,红区代表最大的在野党共和人民党胜出的区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牢牢占据安纳托利亚内陆,仅安卡拉及周边除外,这一大片黄色是国家政治版图的主流基本盘。以伊斯坦布尔为代表的欧洲部分及爱琴海、地中海沿岸无疑是反对埃尔多安的,可惜窄窄一条红带无法与广大黄区抗衡。再看土东南两个代表性城市加济安泰普和更东边的迪亚巴克尔,前者落在黄区,这里土耳其人依然是主流;后者很红,是这个国家最有反骨的库尔德地区,反埃尔多安反得旗帜鲜明。
一篇2016年的旧闻看得我毛骨悚然,讲的是从叙利亚渗透进土东南的“伊斯兰国”在加济安泰普针对库尔德平民发动恐怖袭击,一对库尔德族新人的婚礼现场,一个十四岁男孩引爆炸弹,炸死五十几个参加婚礼的人。“伊斯兰国”对这么年轻的孩子进行洗脑搞自杀袭击,令人发指。叙利亚内战时期,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伊斯兰国”和阿萨德政权四方形成错综复杂的敌对状况,文章把土叙边境的加济安泰普比作八十年代阿富汗与侵阿苏军冲突时期的巴基斯坦边城白沙瓦,各种官方及民间救援组织、间谍、外交官、国际战士、记者、难民等等齐聚加济安泰普,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除难民外,上述各色人等经常光顾加济安泰普市区的同一家星巴克,说得我这个对星巴克没兴趣的人都想去见识一下。
想起2017年在北非偶遇一个给土东南美军基地人员当心理咨询师的美国人乔伊丝,她跟我讲了很多叙利亚动乱期间土东南的情况,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美军基地处境变得异常紧张,乔伊丝说她是整个基地唯一可以走出军营与土耳其平民接触的美国人,因为她不是军人,只是领军方发的薪水而已,假如她跑出去被恐怖分子干掉美军也不管,结果成了整个基地最自由的人。也许乔伊丝也在那家星巴克混过。当然现在情况可能变了,尤其是大地震过后。
最近这次7.8级大地震,震中与加济安泰普相距仅37公里,安纳托利亚板块和阿拉伯板块在这里遭遇,形成地震频发的东安纳托利亚断层。见过安条克的惨状之后,我感到加济安泰普受灾程度要轻得多,虽然离震中更近。这种情况与2008年汶川地震有些相似,北川的灾情要比汶川严重。加济安泰普市中心一栋四层楼倒塌,造成至少154人死亡,这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另外四栋倒塌的建筑造成102人死亡,多数建筑没有遭受重大结构性损坏,但我也看到一些楼房之间嵌着光秃秃的空地,无疑是被地震夷平的街块,空地上堆着未清除干净的瓦砾或未使用过的新建材,说明灾后重建仍在进行中。
除了地质断层之外,加济安泰普还隐藏着一些因历史问题造成的文化断层。
奥斯曼帝国时期,加济安泰普还没有获得“加济”前缀,城市名称仅仅是“安泰普”,它的阿拉伯语名“艾因塔布”(Aintab)更广为人知。从历史来看,这个土东南最大的城市更多时候是属于叙利亚而不是安纳托利亚的,长久以来归叙利亚北方首府阿勒颇管辖,居民构成除土耳其人外还有过相当数量的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库尔德人。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崩解,1918年至1921年的土法战争中,土耳其与法国围绕艾因塔布展开围剿与反围剿,最终土军成功粉碎法军的围攻,艾因塔布脱离叙利亚归属土耳其。1921年,土耳其共和国议会授予安泰普“加济”(英雄)称号。随着城市改名,战前的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土耳其化、同质化的城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剧烈的变化莫过于数万亚美尼亚人在加济安泰普的“被消失”。尽管亚美尼亚人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数千年,但现代土耳其不仅否认帝国末期和一战中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还试图抹去亚美尼亚人曾经存在的记忆。
一百年后的加济安泰普看上去完全是个土耳其城市,它跟阿勒颇的传统联系早已被切断,但由于靠近叙利亚边境,当新的动荡来临时,边界的密封性有可能突然松动,加济安泰普就成了首当其冲承受来自国境线另一边冲击的目标。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加济安泰普在其后几年内接收了大约五十万逃离冲突的叙利亚难民,人口激增使这个原来的土耳其第七大城市一跃成为第六大城市,也使久违的阿拉伯文化重回加济安泰普。
对我来说,这个城市本身吸引力有限,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古老的地理名词:美索不达米亚。抵达加济安泰普就意味着踏进幼发拉底河流域,从这里开始,我要一路向东,过幼发拉底河,再过底格里斯河,开展一趟美索不达米亚之旅。



02
其实,2003年我来过一次加济安泰普,从这里出发坐卧铺火车回伊斯坦布尔,旅行日志里有这样一行:“2003.6.3,Antep→H.Paşa 14:30 4车厢13铺 19.6MTL”,起点安泰普,终到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的海达尔帕夏站,车票钱是一千九百六十万旧里拉。土耳其国家铁路公司运行图上,加济安泰普到海达尔帕夏的列车被称为托罗斯快车,得名于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的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我记得小时候读过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一开篇就写到托罗斯快车:
叙利亚的寒冬;清晨五时。在阿勒颇车站的月台旁停着一列火车,那就是在火车旅行手册中大肆宣传的陶鲁斯山脉快车。这列快车上挂有一节带厨房的餐车,一节卧车和两节普通客车。(陈尧光译本,1979年出版)
小说第一章披露,德本汉小姐(1974版电影中由瓦妮莎·雷德格雷夫扮演)的旅行线路是从伊拉克的巴格达出发,乘火车经基尔库克到摩苏尔,再到叙利亚北方大城阿勒颇,搭乘托罗斯快车穿越安纳托利亚抵达海达尔帕夏站,然后乘坐博斯普鲁斯海峡渡船到伊斯坦布尔欧洲一侧换乘著名的东方快车去往西欧。
托罗斯快车1930年通车,起点是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的海达尔帕夏站,终点是叙利亚的阿勒颇,经营这趟国际列车的万国卧车公司(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同时经营着巴黎到伊斯坦布尔的东方快车,那么,在我想象中,德本汉小姐在托罗斯快车和东方快车上的两段旅程很像如今搭乘同一家航空公司的联程航班,中途在伊斯坦布尔的两个火车站之间“转机”。万国卧车公司是法国/比利时背景的铁路客运公司,把东方快车和托罗斯快车连接起来,一头落在法国,另一头落在法国控制下的保护国叙利亚,这个“联程航班”就成了两次大战之间连接法国和法属中东的一条通道。阿加莎·克里斯蒂安排一位说法语的比利时侦探波洛出现在两列火车上,也算合情合理。
我发现那个年代(《东方快车谋杀案》发表于1934年)的托罗斯快车并不经过加济安泰普。德本汉小姐走过的线路,实际上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力推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基本重合。
一战前新兴的德国渴望拥有一个波斯湾港口,于是出资兴建这条基本上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一战前,现代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领土都属于奥斯曼帝国),其动机与同时期法国推动兴建河内—昆明滇越铁路类而不同,法国人已经控制云南两条重要河流澜沧江、红河的入海口,他们想要染指中国西南内陆。1930年托罗斯快车通车时,柏林—巴格达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只到摩苏尔为止。我判断,德本汉小姐从巴格达出发时乘坐的是米轨列车,终到基尔库克,从基尔库克到摩苏尔没有铁路,只能坐汽车,在摩苏尔住宿一夜后,次日坐上托罗斯快车,沿着标准轨距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经阿勒颇、阿达纳、科尼亚抵达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按照1921年土耳其与法国战争结束后重新划定土叙边界的《安卡拉条约》,两国正是以东西走向的柏林—巴格达铁路作为分界线,它从加济安泰普南边不远处经过,把1921年以前联系紧密的阿勒颇和加济安泰普分隔在两个国家。
这次在加济安泰普逗留,主要目的就是想去看一眼边境线上的柏林—巴格达铁路。来之前已经锁定铁路线与幼发拉底河交界处的一座小城卡尔卡默什(Karkamış),古称卡赫美士(Carchemish),如今属于加济安泰普管辖。
多年前读过历史学者杰里米·威尔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书,记住了卡赫美士这个地名。1911年至1914年,T. E. 劳伦斯在未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之前,在卡赫美士从事了四年考古挖掘工作,直到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每个考古季,他都会在工作之余外出旅行,经常穿着阿拉伯服装,深入探索叙利亚,同时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他后来认为那四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卡赫美士这个地方使我好奇,首先是因为劳伦斯,其次是因为卡赫美士的边缘位置。它处在分隔现代土耳其与叙利亚的铁路线上,此其一;同时,它恰好位于幼发拉底河畔,此其二。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看,幼发拉底河这条地理分割线曾是赫梯帝国和亚述帝国的分界线,卡赫美士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主意已定,剩下的任务就是找到从加济安泰普去卡赫美士的路子。我去汽车站打听,发现没有车辆直达卡尔卡默什,要先到一个叫尼济普(Nizip)的地方再转小巴。又去火车站打探,结果也差不多:乘郊区火车到尼济普,那里有小巴去往卡尔卡默什。
火车站相当冷清,但本身有些可观之处,建筑布局和立面设计采用了水平和垂直的空间结构元素,有种质朴的对称美。外墙采用硬石灰岩,内墙用了软石灰岩,天花板覆以玻璃,这是195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建筑技术。加济安泰普在整个土耳其算很晚才通铁路的,因此这个火车站的建筑风格现代而简洁,据说是土国“第二次民族建筑复兴运动”的特点,而共和国早期建造的许多铁路建筑都带有“第一次民族建筑复兴运动”的痕迹,特点是奥斯曼帝国建筑元素比较多见。如今加济安泰普火车站已开通高铁,但最远只到地中海边的梅尔辛,长途列车都已停运,包括托罗斯快车。1959年,火车站建成时,从距离加济安泰普最近的火车站纳尔勒(Narlı)引出一条支线抵达加济安泰普,并继续延伸到卡尔卡默什,与柏林—巴格达铁路汇合。伊斯坦布尔开来的托罗斯快车不再以阿勒颇为终点,而是终到加济安泰普。火车的到来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件大事,虽然拢共只有一列客车抵达,但市民们仍然蜂拥至车站,野餐、烧烤、观看火车成了当年时兴的一种消遣活动。

03
在市政府对面等公交车,来了一支游行队伍,我的第一反应是:学生声援巴勒斯坦?走近一看,不是,中年人居多,手上挥舞的也不是巴勒斯坦旗。查手机新闻,说是教师团体,抗议针对老师的校园暴力。“易卜拉欣老师不只是被一颗子弹杀害的,他更是被教育制度杀害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很明确教师们的抗议是针对政府的。刚拿出手机拍照,立刻出现一个便衣警察,把我叫到一边说了句什么,起初我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他只是想检查我的随身物品。翻完我的包后,便衣道一声“塔曼”,这个词我懂,相当于“OK”。突然想到,自从加沙冲突爆发以来,我在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包括伊斯坦布尔、阿达纳和加济安泰普以及逊尼派占多数的贝鲁特西区,从未见过巴勒斯坦旗,只在西欧城市和真主党控制的贝鲁特南区见过。其中原因,我想我大概明白。

这个城市教给我的土语小知识,除了“加济”还有无处不在的词语“佛斯特克”(Fıstık),本意是笼统的“干果”,但在加济安泰普专指开心果,因为此地是土耳其的开心果之都。在加济安泰普,开心果普遍到了连面包房师傅都会豪气地在羊角面包表皮洒开心果碎粒。然而,开心果并不是廉价特产,街头干果店里品质上乘的开心果每公斤售价可达500里拉,约合人民币112元。
世界各地都有为土特产造像的爱好,我在江苏盱眙见过巨型小龙虾雕塑,在柬埔寨的白马(Kep)见过巨型螃蟹雕塑,这次在加济安泰普也遇到一座开心果雕塑,造型不算太夸张,基座上竖起两只手,托起一颗比橄榄球大许多倍的开心果,皮开肉绽,露出壳内的绿色果肉。土耳其到处都有开心果酥皮糕点(Baklava),以前在别处吃过,嫌它油大而齁甜,然而在加济安泰普,这个旧有认知被颠覆了。找到一家百年甜品老店Güllüoğlu喝下午茶,1871年开业的,专做开心果酥,出品有好几种,我尝了三款,都非常可口,开心果味浓郁,不过分甜,不过分油。


加济安泰普在土耳其以美食著称,这方面我了解不多,只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食城市名录它榜上有名。中国有六个城市入选:成都,顺德,澳门,扬州,淮安,潮州,都算好吃。一到加济安泰普我就找了有名的Yesemek餐厅吃晚饭,扫码看菜单,先看到一句宣言:“若把世界比做家,它的厨房就是加济安泰普。”可见当地人在吃这件事上非常自信。
吃了两天后,我有点理解了当地美食的两大特色:一个是羊汤,第二个就是开心果酥。第二天午饭去了巴扎区一家非常有名的羊汤馆子叫Metanet,只做早餐和午餐,经典慢炖羊汤配大饼要200里拉(人民币45元),另加一份沙拉35里拉。羊汤可加辣也可不加,我选择加辣,这样更正宗。土东南爱用叙利亚阿勒颇干辣椒粉,其实不怎么辣。汤里除了有炖得酥烂的羊肉还有米粒儿,这种搭配可能是本地特色。在Yesemek餐厅也点了一份汤,大概是基本款的变形或改良版,主要成分是西葫芦,汤里也有羊肉,但切成了碎丁,米粒换成鹰嘴豆。由于西葫芦的用量很大,蔬菜的味道中和了羊肉的腥膻,使汤味更微妙。我看这种实验可以永无止境地变奏下去,Yesemek还提供加土豆的、用各种乳酪、各种豆类的羊汤,菜单上还有一种汤,英文名叫什么Vaccine,看了一惊,再看原文是Çağla Aşı,用翻译软件一照,确是译成什么疫苗,那到底是什么汤呢?看图片,汤里的固形物不像菌类也非豆类,大概是一种我没吃过的当地蔬菜品种罢。


有一天午饭时看到一种酸奶装置,值得一提。打开水龙头后,源源不断流淌出白花花的酸奶,让我想到《圣经》里说的“流奶与蜜之地”。那是市中心广场对面的一个露天馆子,生意好,食物一般,我吃了旋转烤鸡肉切片厚卷饼(Dürüm,有别于更常见的薄得多的皮塔饼),亮点就在像扎啤一样从水龙头流泻而出的酸奶。啜饮之前,我效仿邻桌食客先用手指把漫出杯沿(带尖嘴的锡杯)的半凝固酸奶撮起来送进嘴里,就像有些人喝啤酒时喜欢先享用浮在面上的泡沫一样。

除了酸奶,至少还有三种饮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种是紫红色的发酵萝卜汁,叫“沙尔甘”(Şalgam),味道一言难尽,融腌菜的咸、酸、苦、涩于一杯,还带着一丝甜味。第二种,当地特有的冰罗勒汁(Reyhan Şerbeti),也是紫红色的,用一束安泰普地方所产的紫红色罗勒浸水煮三十分钟,加丁香、肉桂后冷藏,是一种去暑解渴的冷饮。第三种是不含咖啡因的“松果咖啡”(Menengiç kahvesi),据说是用库尔德人的方法制作的,以松果代替咖啡豆烘焙研磨而成。只不过,在开心果之都加济安泰普,这款热饮用的不是松果,是开心果树籽,别具一格,味道也好。我找到铜匠巴扎附近的塔米斯咖啡馆,开在一栋奥斯曼老建筑里,据说1635年开业,论年龄,它比任何一家现存的维也纳咖啡馆都要古老两百岁以上。一杯松果咖啡在这里售价60里拉,折合人民币13块半。
吃喝之余,我在城里闲逛。铜匠巴扎的匠人依然像二十年前一样制作着比人还高的巨型器皿,不知拿来做什么用。伊诺努大街西段有一片“小阿勒颇”街区,显然是叙利亚人聚居区。火车站南边的Forum商场很适合观察本地中产生活,我在商场一角找到了《纽约时报》说的那家星巴克,有个半露天的后院,晚上八点多还坐得半满。或许其中有些人真是“境外势力”?它像《卡萨布兰卡》里的小酒馆,别有一种吸引力,但我只是匆匆瞥了一眼就离开了。可惜这里不卖酒精饮料,也没有酒保在钢琴旁弹唱《时光流逝》,否则我可能会动念坐下来喝一杯。


离开加济安泰普之前又来Yesemek吃了一次,点的是五种安泰普特色小吃拼盘配炸肉丸和藜麦饭。起初想点那种叫疫苗的汤,却被侍应生告知现时不是当季吃不到。我问他“疫苗”到底是什么,经他解释,我终于明白所谓的疫苗实际上是巴旦木的嫩果,中文叫扁桃,颜色翠绿。“疫苗汤”不过是羊汤的又一种改良版,以扁桃果入馔,将我前次吃的汤里的西葫芦换成扁桃,与切成丁的羊肉入锅慢炖,加鸡蛋、奶酪、鹰嘴豆、藏红花、辣椒粉、橄榄油,就成了“疫苗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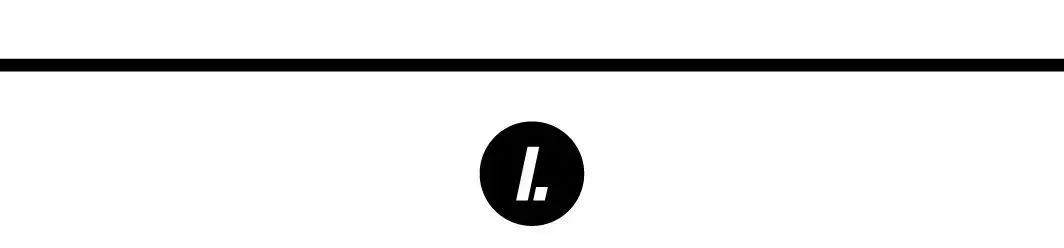
因为公众号规则改变,如果可能,请把我们公号加上星标。以免错过一些精彩的影像。
作者:赋格
闲逛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