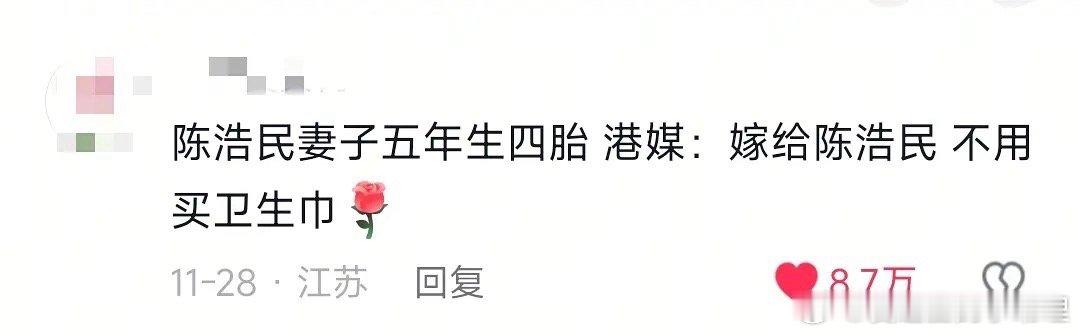一个美国女人故意用英语和辜鸿铭交谈,辜鸿铭没理睬,美国女人冷笑起来:“他连英语都听不懂,怎么配来这高雅的地方!”可当辜鸿铭演讲后,只对那美国女人说了一句话,就让她无地自容。 1913年上海外滩的风带着黄浦江的潮气,钻进汇丰银行宴会厅的雕花窗棂。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无声的角力——穿西装的洋商晃着香槟杯,留洋学子用拉丁语低声寒暄,而角落里,一袭藏青长袍马褂的身影格外扎眼,手里那根象牙手杖在地毯上轻叩,像在数着空气中的傲慢。 那美国女人是纽约报社的记者,跟着领事来的。她盯着辜鸿铭袖口磨出的包浆,还有瓜皮帽下露出的发辫,心里的轻视像气泡一样冒出来。特意用最纯正的纽约英语问他要不要香槟,尾音扬得老高,像是在逗弄不懂事的孩子。 辜鸿铭只是抬眼扫了她一下,眼神淡得像没起风的湖面。然后转过身,继续和身边的英国教授说话,说的竟是柏拉图《理想国》里的洞穴寓言,德语发音带着莱比锡大学的严谨,英语词汇量让她这个报社记者都暗自咋舌。 后来她才从领事口中零星听到,这人叫辜鸿铭,生在南洋,十岁就被送去欧洲,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肚子里装着十几种语言,连西方学者都要找他讨教莎士比亚的隐喻。 主办方请他演讲时,她还在和人打赌他会不会怯场。结果他走上台,长袍下摆扫过台阶,没有鞠躬,直接开口——标准的BBC腔,比她听过的任何播音员都流利。“西方文化是利刃,中国文化是磨刀石,”他说,“没有磨刀石,利刃迟早会钝;只守着磨刀石,也切不开柴薪。” 演讲结束时掌声雷动,他却径直走到她面前。“女士,”他的英语清晰得像冰块撞击玻璃杯,“你刚才说听不懂英语就不配来这里——可你听懂了我的演讲,却没听懂里面的尊重。高雅从不是西装革履的专利,是心里能容下不同的声音。” 宴会厅的水晶灯晃得人眼晕,美国女人却觉得浑身发冷。手里的香槟杯在微微颤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最后只能狼狈地转身,匆匆消失在旋转门外。 那时的中国,正被“全盘西化”的声音淹没。留学生剪了辫子穿西装,文人喊着“打倒孔家店”,好像只有把自己变成“西方人”才算进步。可辜鸿铭偏不,他留着辫子,穿着长袍,用西方人的语言告诉他们:你们追捧的“文明”,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过“和而不同”。 连刚才和他讨论柏拉图的英国教授都点头,说:“他让我想起牛津的老学者,固执,却有骨头。”偏见在实力面前,从来站不住脚。 如今再看外滩的夜景,高楼比当年的汇丰银行高得多,可那根象牙手杖轻叩地面的声音,好像还在提醒我们:文化的高低,从来不靠别人定义;真正的自信,是穿着自己的衣服,也能站直了和世界对话。 你看,百年前那个穿长袍的中国人早就证明了——语言和衣着从来不是高雅的标尺,尊重与自信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