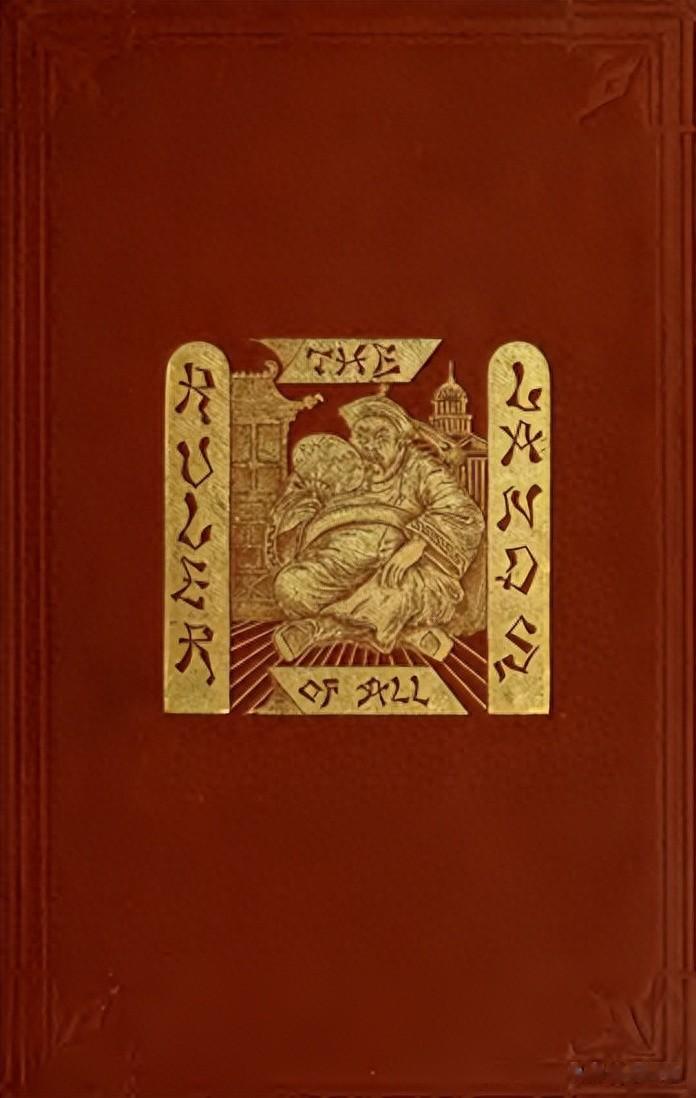
1880年《合众国的末日》书封
(1880年,美国作家P.W.Dooner在排华思潮影响下,写了一部架空史书《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合众国的末日》),号称用“三十年观察数据做演绎,如数学计算般推导”出了20世纪的美国将被清朝移民颠覆的景象。两年后美国排华法案通过。本文《龙星旗永不垂落:1900美国沦陷记》就是在该书基础上创作的架空历史小说。)
第二卷:龙旗飞扬 (1898 - 1901)
1884年定远舰和镇远舰
第五章 龙旗初升1898年,远东甲午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清廷的惨败暴露了其虚弱,但也刺激了部分有识之士寻求“非常之道”。目光,悄然投向了太平洋对岸那片华人血汗浸透的土地。清廷重臣温祥,借考察商务之名,秘密抵达旧金山。
在六大公司戒备森严的密室里,温祥向陈阿福、周棠等核心人物出示了光绪皇帝用朱笔写就的密诏:“着即整备力量,伺机夺取美国西海岸,以为我大清海外之基业,解国内之困局。”
烛光摇曳,映照着陈阿福棱角分明的脸。他已年近花甲,两鬓微霜,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四十多年来,他从一个淘金工变成掌控加州铁路、农场和地下武装的无冕之王,见证了华人从被肆意欺凌到掌控经济命脉的艰难历程。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从一名反抗者,转变为一场征服战争的先锋。
“我们有三百万华人在美,大多青壮,吃苦耐劳,且饱受屈辱,人心可用。”温祥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煽动力,“朝廷已密令北洋水师,‘定远’、‘镇远’等舰即将以访问为名,巡弋太平洋,随时可提供支援。”他打开一个紫檀木盒,里面整齐叠放着一面面崭新的三角龙旗,“届时,只要我们举起这面旗帜,就能让我华夏子民,彻底摆脱这二等公民之命运!”
陈阿福的手指拂过龙旗冰凉的绸面,微微颤抖。这面旗帜,承载了太多血泪和希望。他想起了死去的同伴,想起了艾莉丝……以及那封绝情的信。他将复杂的情绪压下,沉声道:“此事关乎数十万同胞身家性命,需从长计议,周密部署。”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总统府,威廉·麦金利总统正为古巴和菲律宾的事务焦头烂额。来自加州关于华人“不安分”的报告被淹没在众多外交文件中,只被标注为“次要地方事务”。他们浑然不觉,一场风暴正在西海岸酝酿。

1900年旧金山
第六章 烽火旧金山1900年元旦,旧金山。当晨曦照亮城市时,一场精心策划、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开始了。
成千上万的华人,不再是温顺的劳工模样,他们从工厂、农场、铁路枢纽、商店中涌出,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电报局、火车站、市政厅、警察局和关键军营。许多低阶白人警官和士兵还在宿醉中就成了俘虏,他们惊愕地发现,对付他们的华人武装,装备精良,组织严密,战术清晰。
陈阿福站在市政厅的屋顶,亲手降下星条旗,升起了象征大清的三角龙旗。龙旗在旧金山凛冽的海风中猎猎作响,与远处海湾桅杆上尚未降下的星条旗形成诡异而震撼的对比。
“我们不是侵略者,”他通过扩音器,对广场上聚集的、神色惶恐的白人市民和神情激动的华人大声宣告,“我们只是想在这片我们流过血汗的土地上,获得平等的权利,拥有不被驱逐、不被歧视的尊严!”
但他的内心远非表面这般平静。他知道,旗已升起,再无回头路。战争的齿轮开始疯狂转动。
消息传到华盛顿,麦金利总统震惊地从办公桌后站起,双手撑住桌面,难以置信地看着电报:“加州……沦陷?被华人?”他从未想过,那个被视为“廉价劳动力”、“沉默族群”的华人,竟会成为美国本土最大的威胁。“快!派军队去!一定要把那些中国人赶出我们的土地!”他对着国防部长咆哮。
然而,反应迟缓的联邦军队还在集结时,清朝北洋水师的舰艇已在西雅图等地“巧合”地靠岸,卸下了“访问团”名义下的军火和陆战队员。更多的龙旗在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的关键城镇升起。

1880年《合众国的末日》插图
第七章 落基山鏖战美国陆军主力在威廉·R·沙夫特少将指挥下,仓促西进,试图在落基山脉挡住“华军”东进的步伐。沙夫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他对“乌合之众”的华人武装充满蔑视。
陈阿福亲率华人军团主力迎战。这支军队以受过军事训练的华工为骨干,融合了部分同情华人处境的白人冒险家和被解放的黑人奴隶,士气高昂,且对地形了如指掌。
在落基山脉一处险要峡谷,沙夫特的军队陷入了精心设置的包围圈。陈阿福利用了修建铁路时积累的、连军方地图都未标注的小道和险隘。
战斗中,一位名叫约翰·杰克·卡特的年轻美军骑兵上尉表现得异常勇猛。他出身南方贵族,家族在南北战争中衰落,对“北方佬”和“非白人”都抱有深刻的偏见。他率领的骑兵队数次试图突破华军的侧翼,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一次激烈的交火中,杰克·卡特甚至一度冲到了离陈阿福指挥部很近的地方。两人在望远镜中对视了一眼,彼此都记住了对方——一个是目光沉静如水的东方统帅,一个是眼神桀骜凶狠的西方军官。
然而,个人的勇武无法扭转战术的失败。沙夫特的部队被分割、伏击,补给线被切断。华人军队凭借灵活的游击战术和精准的射击,大量杀伤美军。最关键的是,杰克·卡特在一次突击中被炮火震落马下,负伤被俘。
“杀了我吧,黄皮魔鬼!”被带到陈阿福面前时,杰克依旧强硬地咒骂。
陈阿福看着他年轻而愤怒的脸,仿佛看到了多年前那些充满偏见的白人。但他没有动怒,只是平静地命令军医为他治伤。“留着他,或许有用。”他对林茂安说。他意识到,单纯的杀戮无法解决问题,分化、瓦解、甚至转化敌人,同样重要。
落基山脉战役,美军主力惨败,沙夫特少将率残部后撤。龙旗,插上了丹佛的市政厅。通往美国腹地的门户,被打开了。

1880年代美国排华漫画
第八章 东海岸的暗流与南方的抉择美军的连续败退,在东海岸引发了恐慌和巨大的种族对立情绪。针对华人(甚至所有亚裔)的暴力事件激增。
在纽约一栋戒备森严的宅邸里,已步入中年的艾莉丝·范德比尔特忧心忡忡地看着报纸上关于“黄祸”和“华人将军陈阿福”的报道。她的手微微颤抖。她从未忘记那个雪山中的男人,也一直保守着儿子的秘密。
她的儿子,亚历山大·陈平安·范德比尔特,此时已成长为一名英俊而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法律,深受民主自由思想影响。他对这场由“故国”发起的战争感情复杂——既对华人同胞的遭遇抱有同情,又对美国受到的“入侵”感到愤怒,更对那个素未谋面、却被谣传是他生父的“叛军首领”充满困惑与排斥。
“母亲,报纸上说他是冷酷无情的屠夫,这是真的吗?”亚历山大忍不住问道。
艾莉丝看着儿子与陈阿福依稀相似的眉眼,心如刀割。“亚历山大,事情……远比报纸上说的复杂。记住,不要轻易仇恨。”
与此同时,在南方的黑人社区,一种微妙的情绪在蔓延。他们从华人崛起的故事中看到了某种希望。当陈阿福的军队推进到密西西比河一带时,他发布了《告美洲各族书》,承诺废除种族隔离,分配土地,实现各族平等。
许多黑人佃农和底层白人工人开始动摇。当杰克·卡特被俘的消息传回他南方的家乡,他的家族和其他庄园主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不仅来自东方的龙旗,也来自身边那些蠢蠢欲动的黑色面孔。

1900年美军
第九章 新奥尔良的转折1900年秋,陈阿福率领东进军团抵达新奥尔良外围。这座南方重镇由杰克·卡特的叔父,老牌白人至上主义者约翰·洛克等人组织武装负隅顽抗。
战斗在码头区爆发。洛克亲自率领武装民兵,凭借熟悉的地形进行阻击。战斗异常激烈。
关键时刻,被俘后一直沉默观察的杰克·卡特,通过陈阿福允许的、与家人通信的机会,了解到家乡白人武装的顽固和黑人群体面临的镇压风险。同时,在战俘营里,他亲眼看到华人士兵对伤员(无论敌我)的人道救治,也接触到了陈阿福那套关于“平等与新家园”的理念。虽然他依旧抵触,但内心坚冰开始出现裂痕。
尤其当他看到,华军占领区里,黑人和穷苦白人确实开始分到土地,秩序并未如宣传般陷入混乱时,他的信念动摇了。
在陈阿福进攻新奥尔良受挫,双方僵持时,杰克·卡特主动提出,愿意尝试劝说叔父投降,以避免更多无谓的伤亡和新奥尔良这座城市的毁灭。
陈阿福深思后,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是一场豪赌。
杰克·卡特孤身进入守军阵地。面对叔父和同胞的质疑与斥骂,他陈述利害:“我们打不赢的,叔叔。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帝国,而我们……连华盛顿那帮老爷们都反应迟缓。继续抵抗,只会让新奥尔良变成废墟,让仇恨吞噬我们所有人。他们承诺了平等……或许,这是南方的另一个出路?”
洛克的回答是一颗子弹,他斥责杰克是“家族的耻辱”、“白人的叛徒”。子弹未能击中杰克,却彻底击碎了他对旧阵营最后的幻想。他带着伤逃回华军阵地。
“我尽力了。”他对陈阿福说,眼神复杂。
陈阿福看着这个曾经的敌人,点了点头:“足够了。”
当晚,华军发动总攻。内部因杰克事件已然分裂的白人武装,在得到承诺(生命财产安全,承认既得土地产权,未来政治参与)后,部分人选择了投降。负隅顽抗的约翰·洛克战死。新奥尔良,这座南方明珠,升起了龙旗。
杰克·卡特选择加入华军,担任军事顾问,协助稳定南方局势。他的转变,标志着华人征服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单纯的军事对抗,开始向政治整合与人心争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