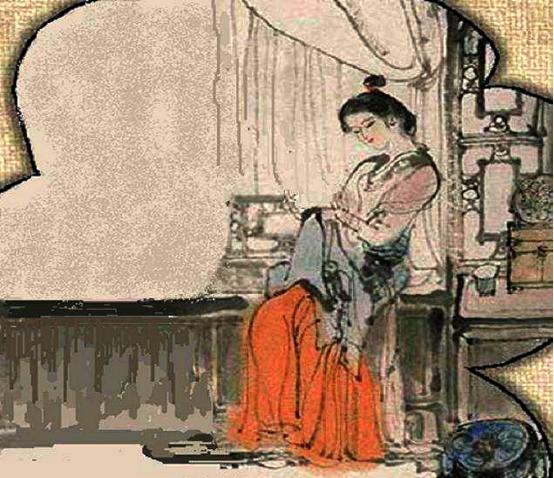元朝文学家姚燧70多岁时,侍妾服侍他沐浴,他一时兴起,便宠幸了侍妾。 这件事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掀起不小波澜,有人说这老头儿越活越糊涂,也有人觉得人之常情没必要上纲上线。 要我说啊,想了解这事儿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姚燧这个人说起。 他可不是普通的文人,在元代文学史上,他的名字能和赵孟頫这样的大家摆在一起,尤其写碑志文更是一绝,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夸他写得跟史书似的有分量。 三岁没了爹,全靠伯父姚枢拉扯大,这位伯父可是忽必烈手下的重臣,直接把他送到理学大师许衡的太极书院念书。 二十岁那年,他写了篇《上宰相书》,里面说的“行汉法、重农桑”把忽必烈都打动了,当场夸他有古人风骨。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个正经儒生,后来会跟教坊司的歌伎扯上关系。 元代的教坊司可不是简单的音乐机构,里面藏着不少官宦人家的女儿。 那会儿有种叫斡脱钱的高利贷,年利率能翻一倍,谁家要是还不上,女儿就得被没入教坊司。 姚燧碰到的那个歌伎就是这么个情况,本来是书香门第的小姐,硬生生成了供人取乐的乐户。 按说这种事儿在当时不算新鲜,可姚燧偏偏要管,不仅赎了人,还认作义女嫁给自己的门生。 这举动在当时挺冒险的。 宋代就有规矩,乐户不能跟良民通婚,元代虽然稍微松点,但士大夫家里扯上这层关系,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 赵孟頫说他有侠气,可王恽在《秋涧集》里骂他坏了礼教纲常。 最有意思的是,这歌伎后来还真把儿子教成了进士,算是给姚燧争了口气。 如此看来,姚燧这人做事确实不按常理出牌。 七十多岁闹出宠幸侍妾的风波时,有人翻出他当年救歌伎的旧事,说他骨子里就不守规矩。 那件事的关键证据,是侍妾贴身肚兜上绣的诗,“八十年来遇此春”这句子,后来被明代的冯梦龙写进了话本里,愣是编成了因果报应的故事。 不过据《牧庵集》里的年谱记载,姚燧其实只活了七十七岁,这“八十”明显是夸张了。 现在去故宫博物院,还能看到一件元代的素纱绣牡丹肚兜,跟文献里说的“茜色罗肚兜”材质差不多。 专家说这种贴身衣物上题诗,在元代其实不算罕见,算是当时一种私密的情感表达。 可放到姚燧身上,就成了文人集团攻击他的把柄,毕竟一个主张“父母在不远游”的儒臣,自己却闹出这种桃色新闻,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这件事最让人琢磨的,是它背后藏着的元代社会矛盾。 一方面儒家伦理还在讲三纲五常,另一方面异族统治下的社会规则早就变了样。 姚燧帮忽必烈搞礼制改革时,把“父母在不远游”写进典章,转头自己就为歌伎破了规矩。 他主修《世祖实录》坚持直书其事,可自己的私生活却成了别人嘴里的闲话。 这种矛盾,怕是每个在元代做官的汉族文人都深有体会。 毫无疑问,姚燧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私生活问题。 他们想守住儒家的底线,又不得不适应蒙古统治下的新规则,这种撕裂感在姚燧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要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真不容易。 你说他守礼吧,他偏要挑战当时的规矩;你说他放浪吧,他又实实在在做了不少好事。 或许这就是真实的人性,没必要用非黑即白的标准去衡量。 就像他写的散曲里说的,“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既有儒家士大夫的担当,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气。 如此看来,七十多岁那场风波,不过是这个复杂人物晚年的一段小插曲罢了。